佛祖说,对“我”别太执着,会好一点
原标题:佛祖说,对“我”别太执着,会好一点
在消费主义社会里,作为生活的主体,我们的个体需求被无限放大,某种程度上,“我想要”的想法占据着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当“我”的感受成为活着唯一重要的部分,我们也会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
“我”真的存在吗?过分执着于自我,会造成什么后果?痛苦的根源,又来自何处?
讲述| 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01.
现代人视野里的“我”
消费社会与物质主义会给现代人带来各种“苦”,现代商业利用人类贪求感官享受与意识习惯性地攀援的特点,不断地制造、渲染、烘托,乃至最终植入消费主义的底层逻辑,也就是“我们”都是消费者,而商品能够给人们提供终极的幸福感,是证明“我们”存在价值的重要符号。
为了证明“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需要无限制地彰显“自我”的需求和感觉,比如“我高兴”、“我悲伤”、“我沮丧”、“我爽”、“我能”、“我行”、“我可以”、“我想要”等心理活动,这背后都紧紧扣住了一个不大会被质疑的关键词,那就是“我”。
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人类的思想历史,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社会中,个体“我”的意义往往都是在“天与人”、“道与人”、“上帝与人”的关系模式中去定位的。简单解释的话,那就是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就会在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精神秩序里去理解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虽然人们拥有个体的差异化意识,但每一个“我”始终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存在秩序,所以往往会表现出某种谦逊、节制,乃至卑微。
比如苏格拉底虽然被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审判,但是他的申辩词中却明确地回答,他信神。只是他所信的与雅典民众所信仰的可能并非一致。而孔子虽然强调人际伦理的关系,但也会讲“祭神如神在”,也就是虽然无法绝对肯定神灵的存在,但仍然要如同祭祀真神一样严肃以待。

《坠入》
不过在庄子的《齐物论》中,他提到的是“我”与“物”的交互与统一,这和前面的“天—人”,或是说“神—人”关系,显然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一般被称为所谓的“忘我”体验。
如同《齐物论》结尾处的那个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一样,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则忘记自己是庄周,等到醒来,才恍然有觉。但是庄子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庄周梦见成为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成为了庄周呢?这样的观点无疑可以很轻巧地消解掉那种僵硬的“我”的主体意识。
其实,无论是道家的“忘我”,还是古印度修行沙门追求的“梵我合一”,背后都代表了人类精神的某些真实体验。 在传统社会的人类精神世界里,“我”并不是像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这样,好像是某种被抽离出来的个体,和外部世界形成主客分明的二元对立,而是能够感受到与万事万物的内在连接。
在艺术中获得类似“忘我”体验的音乐家并不少,比如著名钢琴家朱晓玫是演奏巴赫作品的专家,她曾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自己曾经有两三次演奏巴赫的“忘我”体验,她说在那个时刻,她似乎进入一种状态,忘记了所谓的技巧和时间的流逝,也忘记了观众,只感觉到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正是这种“体验”,让她把老庄的道家和巴赫的音乐联系了起来。
不过,现代哲学似乎对这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体验并不那么信任,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某种理性化的逻辑推论,比如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就一方面认为感官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一方面又无法彻底否定人的“存在”,因此当他说出“我思故我在”时,他其实要表达的是,“我”作为一种认知基础,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
现代思想界在关于“自我”的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讨论,比如以精神分析闻名的拉康,就提出过所谓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的“自我”其实是在婴儿发育的某个阶段,通过对他人(镜中人)的认识来建立起“自我”的存在,也就是所谓“自我意识”的产生,但这个自我意识是撕裂和不连续的,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同一性的“自我”。
拉康循着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句式也说出一段晦涩的话:“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思想,所以我在我不思想的地方存在。”其实,我并不能肯定拉康这句玄妙分析背后具体的含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拉康以及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一直在挑战“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这一观念。

《坠入》
不仅是哲学领域,在脑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看法。著名的脑科学家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曾在《谁说了算》这本书里,以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自我意识”其实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幻觉。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分辨和看清呢?扎尼加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担心的是,了解真相会叫你产生生存危机的话——我想说,没那么严重。毫无疑问,你仍然会觉得控制着自己的大脑,一切归你说了算,归你拍板定夺。你依然会觉得某个人,也就是你,坐在中间做出决定,拉动杠杆。这是一个我们似乎怎么也撼动不了的“超级小人”想象:我们总觉得有一个人,一个小人,一个灵魂,掌控一切。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数据,知道它是以其他某种方式运作的,我们仍然有着这种大权在握的压倒性感觉。
扎尼加的结论是,“自我”虽然从认知科学角度来看是一个骗局,但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中,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个真实的“我”,而无法摆脱这种幻觉。
因为一般人无法看清这个所谓的“自我幻觉”,所以在主流的认知里,我们都几乎毫无疑问地会肯定“自我”是真实的存在,在各种相关的理论体系和道德实践中,都会以此作为前提去讨论各种问题。
比如著名的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那本大为流行的科普读物——《自私的基因》里就曾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类作为生物性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个基因机器而已,而基因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试图复制自己,让自己在基因库里不断壮大。人类的自私根源其实在于基因的自私,是基因主导了人类的行为选择,甚至包括某些利他的行为,也只不过是出于保护自己来进行基因复制而已。
这当然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一个非常合理的为“自我”辩护的观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在经济学领域里,早期像亚当·斯密那样,不仅强调人有自私的一面,同样认为人同时具备关心他人福祉的精神动机,因此也会具备正义和仁慈的道德品质。
而在今天,我们受到一种狭隘的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对于个体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极端欲望化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越来越与世界脱钩,这其实是因为, 现代社会越看重“我”,就越容易与他人开始产生疏离感,很难与他人有深层的连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个“我”不仅僵硬呆板,而且是孤立、孤单、孤独的。
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大家表面上看起来拥有了更为便捷的交流工具,但结果却是,年轻人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玻璃球,彼此只有浅表的互动,难以形成彼此之间深度的内在连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年轻一代对于“我”的认知有密切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我”到底是什么?
02.
原来没有“我”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构成了判断是否为佛法的三个标准。可以说,如果不承认“无我”,基本就可以宣称那不是佛法。但是要理解“无我”,要从认识“我”开始说起。
听到这里,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还需要去认识吗?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在《那先比丘经》里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弥兰王因为精通各种学说,因此想找一位智者来与之交流,于是有大臣推荐了一位比丘前来,这位比丘就是那先。
弥兰王当然想要挑战一下这位被誉为智者的僧侣,首先就问道:“谁是那先呢?头是那先吗?”那先回答道:“头当然不是那先。”接着弥兰王问,那耳朵、鼻子、嘴巴、颈项、肩臂、手足、腿脚、肤色、苦乐、善恶、身躯、肝肺、心脾、肠胃等等,是不是那先呢?那先比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接着那先比丘开始反问弥兰王,车轴、车轂、车辐、车辋、车辕等组成部分,乃至车运动所发出的声音,哪一个才代表车呢?弥兰王回答说,这些都无法代表车。那先比丘便问,那什么才是车呢?弥兰王沉默不语。那先比丘这时候才引用佛所说的道理来回答,也就是,所有这一切组成的部分合在一起,才能称为是“那先”或者是“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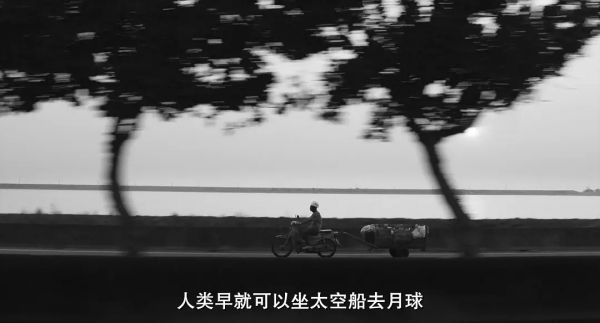
《大佛普拉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认知对象进行层层化约拆解的认知方法,在佛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析空”,也就是为了要认知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以从空间、时间等角度来进行化约式的分析。前面那先比丘和国王的对话,显然就是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最终发现在每个组成部分中都无法找到“我”的本质,由此便推论出“无我”的结论。
比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地剖析开来,从皮肉、筋骨往深处去观察,最终看到的也不过是基因、蛋白质或是粒子而已。但基因、蛋白质和粒子就是生命的本质吗?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测量极限而已,我们能借此推论说,基因和粒子能代表“我”吗?它们只是“我”的组成条件而已,如何能说它就是生命的本质?从基因和粒子中间,看不到“我”的特质。
而从时间流逝的角度,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比如那先比丘就问弥兰王,从吃奶的小时候,到了长大的时候,这两个身体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弥兰王说,身体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先比丘又问:回到受精卵的时候,到变成有肌肉、骨骼的时候,到出生以后,长到几岁的时候,还是过去那个受精卵吗?当然都不是。
有时候想想,我们的人生不过是无数的时空切片,到底哪一个才是你?如果用高维度的视角看, 我们在尘世中走来走去,忙来忙去,每一个时空的切片好像是你,又不是真的你,你找不到那个单一的、不变的、本质的你。十五岁的你是你,四十岁的你也是你,请问他们是一个人吗?既是又不是。
显然,这就是从线性时间的角度来拆解“我”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有一个“我”存在,有某种恒常的本质,而我们借助时间、空间的拆解,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五蕴身心中,根本找不到“我”的本质存在。

《山中的汤姆先生》
这种利用“析空”的方法来层层剖析我们身心的逻辑,和西方哲学史中的“忒修斯之船”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的哲学家普鲁塔克曾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假如我们把名为“忒修斯”的船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掉当中的木板,直到最终全部更换一遍,那么这艘“忒修斯”还是最初的那艘船吗?
在西方哲学史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很多答案,但是如果按照佛学的思维,正如前面的那先比丘所回答的那样,人世间无常变动,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那么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乃至未来的“我”究竟是同一个“我”,还是不同的“我”呢?这个时候,佛教就要我们去体会这种“相续而不同”的存在状态,这就是佛学中比较初步的关于“无我”的解释。
这里还是拿比喻再来总结一下吧,“我”其实就如同一条河流,看上去连续不断地变换,但是它仍然维持着一种让人可以识别的轮廓,它有自己流动的方向与形态,但是你却不能说,哪一滴水就是这条河流,你也不能说,前一秒的那一朵浪花就是这条河流。你会感觉到过去、现在、未来奔流的每一滴水珠、每一朵浪花,乃至每一个漩涡都是这条河流,但同时又都不是这条河流。
03.
如何观察和体验“无我”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大家似乎很容易在理性上了解“无我”的内涵,并且应该也开始理解佛学中对于“无我”的这种“相续而不同”状态的阐释。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这种相续但不同的状态,其实是难以体验的,因为这和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式相关。
在鲁迅非常喜欢的《百喻经》中,佛陀曾经举过这样一个譬喻故事来形容我们的这种无知,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愚痴的人,看到池水中有黄金的倒影,便拼命去打捞,结果一无所获。等到水面平静之后,黄金倒影重现,他又开始去捞,如此往复,不知疲倦。
此时他的父亲寻子来到池边,见自己儿子如此作为,便询问为何,这位愚痴的儿子便如实以告,父亲便告知他,池水中不过是飞鸟叼到树枝上的黄金的倒影而已。
佛陀接着便讲说了一个偈子:“凡夫愚痴人,无智亦如是,于无我阴中,横生有我想。如彼见金影,勤苦而求觅,徒劳无所得。”意思是说,一般人其实都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在我们的五蕴身心中,硬是产生了对于“我”的某种想象,但是这就好像在池水中去打捞黄金一样,是注定徒劳无功的。
那么,我们要该如何观察和体验“无我”呢?
首先,我们可以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思维方法来观察,比如佛陀在经典中要弟子们时刻去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比如观察身体从时间、空间、形状乃至运动等角度,那里面到底存不存在一个“我”,乃至进一步从受、想、行、识等“心识”层面也同样去观察,我们的感受、取像、念头迁流乃至意识分别中,到底有没有一个“我”存在于其中。如此反复思维,就可以让自己对于“我”的理解,慢慢地看得清楚,减弱执着。

《阿弥陀堂讯息》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吧,当我们早上兴冲冲地赶到公司上班,但可能运气不好,手头的事情处理地不够妥当,或者仅仅是因为上司的误解,将你劈头盖脸地责骂了一顿。现在的你,当然会心情沮丧,还会感受到委屈和愤怒,甚至整个上午包括午餐时,你都仍然耿耿于怀,就算是不再回味当时的场景,内心中的压抑与晦暗感受也是很难消散的。
此时,你或许可以这么思维:的确,现在的“我”非常难受,产生了很多烦恼。那么,到底是“谁”在烦恼呢?“我”不过是由身心组成的现象而已,那么到底是我的头烦恼,还是我的胳膊烦恼,抑或是我的嘴唇烦恼呢?
当然,你会马上得出结论:是“我“的“心”在烦恼。而“心”又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心识的作用,可以划分为“受、想、行、识”这几个不同的认知阶段与不同方面的作用。那我们可以继续去思维:早上上司的那顿责骂声,明明已经过去,当下的“我”根本没有再听到,同样,我也看不到当时上司的那张愤怒或扭曲的脸,偷偷瞄一眼的话,此刻的他/她或许还正在开怀大笑呢!
也就是说,在责骂发生时的“我”到了现在,其实早已经时空转换,无常变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早已经远离上午的境界,那为什么“我”仍然会为上午的事情焦虑不安呢?
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你的意识里预设了有一个“不变”的“我”,所以上午感受到沮丧的那个“我”,被你硬生生地带到了中午、下午,乃至是第二天,而这不过是因为你在那个不愉快的心境里错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就会背负着这个受伤的“我”,度过一个个白天与黑夜。
执着比较深的人,甚至就算是再长的时间,也很难化解某些场景下所受到的心理打击,因为那个心理所臆想出来的“我”过于坚固,也因此所感受到的苦楚也就特别的深切,直到身心疲惫,情绪崩溃,再也没有心力去造作这种关于“我”的幻觉,才能慢慢地从情绪的低谷中走出来。
尾声.
在这里,让我们回到那段佛陀的教导:“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是真实正观。”
为什么我们会苦?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想要主宰,而想要主宰,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认知,也就是有一个真实的“我”和这个“我”想要主宰、控制的对象,也就是“我所”。
所以,在“无常”的世界中,我们感受到个人的无力与困惑,也就是某种无时无刻的苦感,而这种无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一般认为的那样,你不够优秀、没有好运气等等,而是你建构起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我”。在这之后,所有的一切事物,不管是你喜欢的,你讨厌的,乃至你无感的,都将与“我”牢牢地对立起来,这才是我们今天为何“越努力,越痛苦”的最为深层的原因。
本文整理自成庆主讲的节目《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的第10集,有删减,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编辑部诚意推荐,看理想年度力作!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长按海报识别二维码,进入节目
音频编辑:夏夏、小蒲
微信内容编辑:汁儿
监制:猫爷
头图:《请回答1988》
转载: 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xingyj@vistopia.com.cn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佛祖说,对“我”别太执着,会好一点
有些东西不必太执着
玉帝为什么要等如来佛祖降伏孙悟空后,才请出三界最高级别的大神
人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痛苦
人生多苦累,何必太执着
男人对身高到底有多执着?
我说网友别太缺德了,这个飙我看是走不出去了!
西游记中,为什么如来佛祖只能降伏孙悟空,却杀不死孙悟空
既然五行山封压不住孙悟空,那佛祖为何还要折腾出五行山?
无论多难,别忘了,会好的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76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709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76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2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33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5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80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8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56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