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罗新对谈:写作梁启超,也是在重新发现“人”
原标题:许知远、罗新对谈:写作梁启超,也是在重新发现“人”
近些年,作家许知远因访谈节目《十三邀》为人所熟知。不过,依照他多年前的说法:“做视频节目,只花费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力在写关于梁启超的新书”。2019年,这个写作计划的第一卷《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面世。这本书讲述了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再到上书清帝、办报刊至戊戌前夜的故事。作为一部转型之作,初尝历史写作的许知远,在这本书里也如他笔下的梁启超一样,面临着诸多的挣扎,其中之一就是——是遵循传统的学术写作,还是以更丰沛的笔触回到当时更具象的历史现场?
很多人都会把梁启超称为“我们的同代人”,他生活的时代正经历新旧之间的剧变,每个人内心的焦灼、迷茫与期盼,与当下的世界形成不息的共振。许知远也并不回避这点,他希望借书写梁启超思索大的历史方向,更重要的则是思索每一个身处转型时期的人如何面对自身的彷徨。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许知远推出了《青年变革者》的续作《梁启超:亡命(1898—1903)》,接着讲戊戌失败之后梁启超的流亡之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阅读梁启超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好的历史传记对我们如此重要?9月2日在北京的新书分享会上,许知远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单读》主编吴琦、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以“重新发现人”为主题,就以上话题展开了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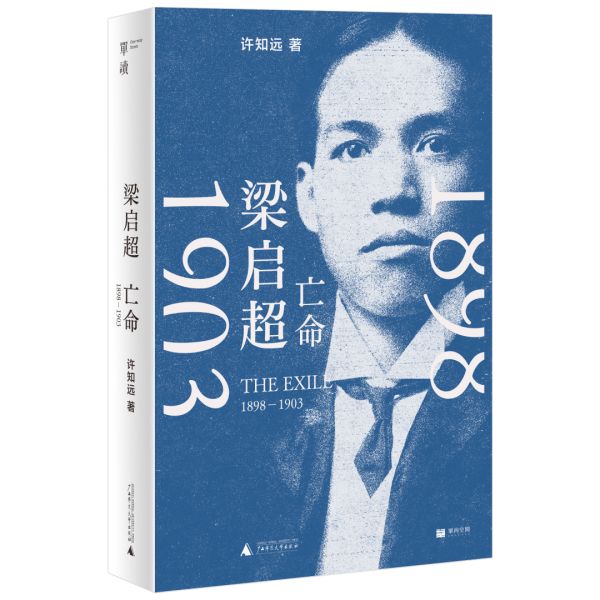
《梁启超:亡命(1898—1903)》,许知远 著,单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整理 | 刘亚光
01
历史写作中的“我”
罗新:这本书我读得比较早,书并不薄,但我还真是用了比较短的时间读完。我想不只是对我来说,绝大多数的读者过去可能都不会读到有关梁启超的这么多生动的细节。所以整个阅读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我自己觉得这本比之前出的第一本要好,我看到豆瓣上评论说第一本书里有“过于鲜明的许知远”。这其实也是我最近几年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学者写得最多的传统学术论文、著作,其实并不会反映太多“我怎么做研究”的经历,而是反映我做了研究以后怎么把它呈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遗憾。这个题目是我找到的,那么怎么能够把“我”放进去,这可能是我们传统的历史写作比较忽略,甚至是禁止的。但如果我们看国外的一些作品,其实对这种平衡有更好的把握,比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讲到作者是怎么想到一些研究困惑的。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适应多样性的写作?如果我们习惯了过去的那种写作形式,越是专业人士越是难以接受别的可能,觉得如果把自己放进去得多了,学术性就少了,我觉得这应该打个问号。
吴琦: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可能提供了新一代读者进入梁启超的一种路径。我想每一个时代比较年轻的读者,永远都需要有一些新的阶梯能够帮助他们和比较久远的事物建立联系。这种联系还需要是非常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化的。
许知远:从写第一卷的时候,我从梁启超的相关史料中清晰地看到王朝的嬗变、权力的更迭、语言的变换、民族的兴衰。他的一生从1873年到1929年,那是整个中国巨大的转型期,包括学术思想、生活习惯、城市面貌、服饰样态,等等,都发生着剧变。梁启超是一个我们窥见宏大思想变迁的窗口。不过,我们描绘一个思想人物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他孤立地活在他的概念世界里。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横滨,在华尔街,在种种具体的气氛里办《新民丛报》《清议报》。我写作的时候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那些具体的人如何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比如他在华尔街见到J.P.摩根,这是一个奇妙的相遇,摩根的托拉斯系统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对经济的看法。
除了通过梁启超看到那个时代中国的变迁之外,其实我也希望能借此体会人们面对世界变迁时候的心态。一个过去的读书人,不会像梁启超那样突然体验到全球旅行过程中无数新事物带来的快感和刺激。当梁启超看到电报的时候,那种冲击和我们今天看到ChatGpt(聊天机器人程序)的感受是一样的。这种目睹加速变化的世界带来的震惊,也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
第三卷我会写到中国留日的学生,那时候的世界仿佛在迅速缩小,湖南、广西、四川的学生们突然跑到横滨,在东京上学。他们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中,一方面,清王朝本身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传播来的新概念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这些都让人感到迷茫而焦灼。人无法消化新世界的时候,往往会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革命军的兴起用的也都是最直接的词汇和口号。我非常想去探寻梁启超在这种时代的恐惧潜移默化进入人心的氛围中是什么感受:百日维新失败了,自己最亲密的人死在菜市口,朋友四散等等。我也特别想写梁启超的那些同代人,他们当时的想法,比如,梁启超之前在上海的朋友孙宝瑄,会在日记里写到他观察梁启超的变化,他发现梁启超变得不一样了,感慨梁启超成为了东亚的奇人,等等。虽然这是有关梁启超的故事,但我特别希望读者们能在书里看到普世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有复杂的因果。我想,如果没有19世纪广东人的移民现象,很多奇妙的相遇也不会发生。所以我会特别希望在书里写出人和人的这种命运感。有时候,这种命运是被你的性格决定的。1895年,人们可能处在同样的起跑线,同样一个巨大的浪潮打来,有的人迎着浪前行,有的人在恐惧和忧虑中自我麻痹或者躺平。我们看到汪康年成就了梁启超办《时务报》,在1898年的大变化之后,他依然在努力,试图在租界给他的自由、清王朝给他的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很可惜,他1911年去世了,死在革命到来的前夜。还有同样办报的汪大燮,1895年在北京陶然亭办《万国公报》,1902年他变成留日学生的监督,得以和梁启超在日本重新相逢。他们总以某种方式契合,所以命运非常奇妙。
所以的确,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意在追寻学术,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对青春的某种回应。1998年,我在北大读大三,罗老师开一门中国通史,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在北大微电子系上课,马上要学令人恐惧的量子力学,当时支撑我度过每天的热情来源就是听别的系的课。我听到罗老师讲完魏晋的时候说,中国历史最迷人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传统太不重要了,一点都不迷人,我们应该学习一些更当代的东西。不过,差不多同一时候,北大请了唐德刚先生来讲座,当时我对他提的“历史的三峡”这些概念还都是一无所知的。我就记得他在报告厅里说“胡适跟我讲……”,我当时就很震撼:还有人认识胡适,从来没有觉得历史离你这么近,尽管1962年去世的胡适,跟当时的我只隔了30多年,没有那么远,但当唐德刚先生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巨大的亲近性,原来你是可以跟他们有关系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北大当时还有地方卖废旧的英文杂志,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代周刊》都是我们接近外部世界非常重要的窗口,那时候的主编就是后来写《乔布斯传》的艾萨克森。我记得我有次读到《时代周刊》做的20世纪的回顾,里面讲到爱因斯坦这类科学家,也讲了列宁这样的政治人物,还写到了很多娱乐人物,这当时也令我惊讶,因为以前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娱乐人物能够写出这么深刻的东西。到今天我还记得主编当时写作的导言,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改变世界的方式,一些人通过“抵达”——比如列宁1917年抵达了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有一些人靠离去……我当时就被这个语言震撼了,这些很具体的阅读经验塑造了我对历史传记最初的兴趣,这种兴趣也确实不是学术上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学术的理解是偏狭的,认为学术就是枯燥、严肃、无趣,一旦富有趣味性学术就变得很可疑,但我们看司马迁的写作就非常生动有趣。我觉得历史传记应该是引人入胜的,西方传记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分类,很多传记作家都希望通过记述笔下的人物来反映时代的剧变,比如我特别崇拜的《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凯恩斯传记需要很多经济学知识,他需要自己去学,然后把自己对经济的理解也会代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我其实也希望能够表达一种隐隐的雄心,就是通过我的写作传递我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罗新:我们写过去人的故事,这个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认识过去,了解过去,反过头表达我们自己,写作当中无论你写不写“我”, 我们写过去的人,最终呈现的都是“我”,很大程度上要呈现“我”。刚刚对谈中,我想到我的导师田余庆先生,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 ,当时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印得并不好,他把书送给他的老伴,并在上面写了一行话,一直到师母去世,我们才看到老师写的这句话是什么,不是说感谢之类的,他们那一代人很含蓄,大意是说,我出的这本书送给你,你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我。

活动现场。(单读/供图)
02
历史传记对我们为何重要?
罗丹妮:许老师的表达让在座的人感觉到传记中“人”的魅力,我很想问问罗新老师,您有没有受什么传记影响很深?此外,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历史上的大人物,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回避他,然而您却选了一个不知名的北魏宫女给她写了传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为什么?
罗新:应该来说,最近越来越多的作者都在进行一种崭新的历史写作。我的师兄李开元近几年因为写《秦崩》《楚亡》《汉兴》,读者很多,他最近说,很多学者“研究”历史,但我更像“写”历史的。我有些不太同意这个分类,其实大家都是写历史的,我之前长期研究那些非常枯燥的问题,写出来可能只有几个人读,比如名号研究。但最近我也开始尝试做些别的历史写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历史写作,都是为了揭示一些过去没有人揭示的东西,差别只是写法。刚才许知远说要建立新的写作可能性,我很赞同,今天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展示历史写作的各种可能性,最终是破除唯一的标准。
说到传记,我们可能都受过传记的影响,但就我个人而言,进入到知识世界不是读传记,第一个对我有重大影响的是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我在大学毕业之前读的所有东西都比不上这本书带来的震撼,当时我在武汉工作,外面突然凉了,我站在阳台上喘不过气来,这种喘不过气的经历后来又发生过一次,就是读我老师的研究,我觉得我消化不了,对我来说过于强大、强烈。我读过很多传记,我不觉得可以仅仅用传记的眼光来看许知远写的梁启超,这就是通过一个人来写历史,许知远也说希望通过写梁启超展现一个时代,我写《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也有这个想法,但可惜材料比较少,确实比较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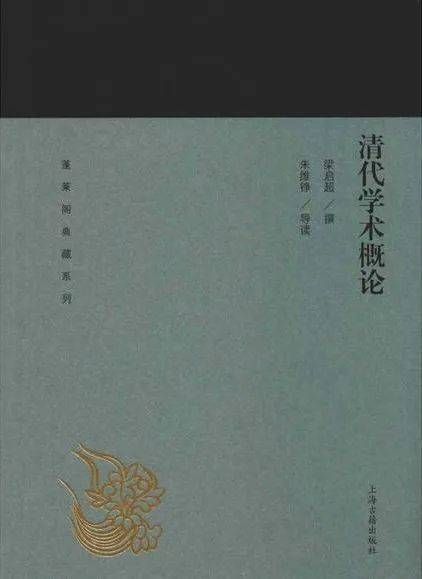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
罗丹妮:在某种程度上,梁启超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梁启超看时代是一种中心视角,而北魏宫女是相对边缘的人物,想听听两位老师对边缘和中心的理解。
罗新: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即便是梁启超,相对于慈禧,后来的孙文、袁世凯,他真能算中心吗?其实也是一个边缘人物。一个秀才是中心还是边缘,要看历史的聚光灯打在谁的身上。其实只要一个人的身上有足够多的材料,一个看似边缘的历史人物也能延展出一个特别大的世界,世界可以大到没完没了,每个人都可以单独成为独特的中心。
许知远:我非常同意,就像广东过去是中原文化的边缘,但到了近代成为一个接收新思想的阵地。梁启超看起来他是中心人物,但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某种边缘者的逆反心理来进入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似乎变成生活中很边缘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位居非常中心的位置。梁启超是那个时代的超级明星,读书人扮演着非常中心性的角色,即使他们遭遇过很多困惑。
吴琦:刚才听罗老师讲,也唤起了我自己的回忆。我觉得人更多的时候是被一个具体的人教育、影响、激励的,不一定是通过传记这种形式。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知识和传统的当代化身,当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这个感受是最深刻的。
我个人想特别问许老师的是,当梁启超的故事被你挖掘出来,抵达学术世界之外的读者,你会期待它能在读者中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许知远: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反应,但至少我自己这里已经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罗老师可能能理解这种特殊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受过专业历史训练,对19世纪的历史一开始完全没有头绪,断断续续写了八年,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慰藉。最近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历着变化,我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非常烦躁,在外界的压力中,晚上一边听音乐,一边写梁启超的时间,对我来说像一个安全屋一样,我可以躲进去。而且每当我想到,梁启超在做那些影响很多人的事情的时候,也在遭遇无数比我剧烈得多的糟心事、生死之忧的时候,也会感到被宽慰。他在那个世界里遭遇重大的挫败,被迫流亡海外,随时都可能灰飞烟灭,但最后居然创造出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最近我们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书店,其实在东南亚、澳洲、新加坡,现在的很多华人学校都是康梁当时创办的,我其实也很想体验一下,当时这些人怎么到一个异乡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在东京开完店,我想可能还可以在温哥华开。写梁启超让我突然对人生中的莽撞产生了新的自信。我记得上罗老师课的那个时候,大家是支持莽撞的,时代的气氛也很莽撞,过去十多年,大家越来越谨慎。客观上确实各种机会在减少,大家也更加拘谨,担心各种各样的评价。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不是很在意别人会怎么评价这本书,因为梁启超也被同代人各种不理解和批评,但他始终坚持做下去。
历史为什么动人,一位英国作家曾说过,传统是对死去人的民主,不能因为一些人逝去,他们的声音就从此消失了,他们仍然有发声的权利。这个发声,会阻止当下的自我的傲慢,也会安抚我们的自我怀疑,这是我写历史很深的一个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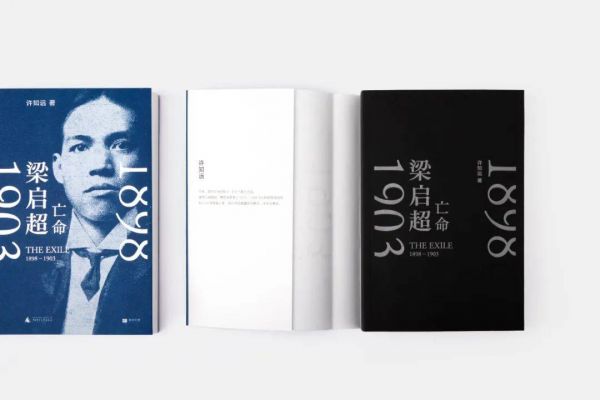
03
回到具象的历史现场
罗丹妮:为学术写作和为大众写作相比,对象是不一样的,许老师这本书跟别的书不太一样,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不同于学者的问题意识,学者写梁启超会具体回应一个领域的专业问题,但许老师从一开始对梁启超充满的是个人的兴趣,我会把这种写作称为将心比心的写作,起点是“我”对一个同样身处巨变和重要时代的读书人单纯的兴趣,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词——笨拙,许老师用了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我要了解这个人,就是跟随他的脚步,他去了哪里,他在那个情况下见了哪些人,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这是历史学家或专业学者不会做的事情,把写作对象当成具体可以认识、了解的人去看待,才会有那么多的细节、行动,从这一点上这种写作是谦虚的,不妄想一下子理解他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变化或是不同道路的选择,而是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一个人境遇的变化,这是真正能够亲近人的写作。
读者:除了写梁启超,许老师也做《十三邀》的节目,一个是接近历史人物,一个是接近当下的活生生的人,这其中有没有相互影响?
许知远:我写书的时候经常会选一首合适的歌听,比如写序言的时候我听的就是一个电视剧《特工科恩》的插曲《The Spy》,这个剧讲的是60年代一个以色列特工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潜入敌国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要写的序言情感就很相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一个人面临一场巨大冒险时内心的活动。这个音乐非常好听,它让我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冒险者必须拥有一种内在的松弛,否则他就会立刻被摧毁。这是音乐带给我的非常强劲而具体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拍节目和写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作的时候时空经常是会交错的。拍《十三邀》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里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表达。明天我如果把罗老师带到吉尔吉斯斯坦,他的情绪会被那里的空间迅速影响,做出和今天在这里很不一样的表达。所以我后来特别想表达不同的时空会对人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因为没有人生活在抽象的思想世界或者是历史世界中。
读者:许老师是因为特别想研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才开始写这本书,还是主要对梁启超这个人物特别感兴趣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为什么以梁启超为切面?
许知远: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记者,梁启超当年也是新闻业的风云人物,而且他处在的历史时期确实是一个中国大转折的时段,这种丰富性很吸引我。其实那个时段里面很多人都值得写,严复、林语堂、梁启超,找个人开始都行。我选梁启超硬着头皮写,写着写着雄心就开始不断膨胀,一开始只想写一本,后来变成三卷,现在计划写五卷,而且在写完第一卷时,我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他只是我更长写作计划的开始,通过写梁启超我又对李鸿章产生了新的兴趣。李鸿章从1823年出生到1901年去世,贯穿整个19世纪。王朝盛极而衰,他做过翰林院学士,后来又大兴现代企业,最后迎接一个屈辱的结果,他代表着中国人跟权力的一种关系。
我也想写李鸿章,如果能写完,之后我还想写林语堂。林语堂出生在1895年,正好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年份。林语堂最负盛名的是英文写作,他在中国最困苦的抗战时刻试图重新唤醒那个古典而美好的中国,这种想象也影响着西方世界。我希望能够在他身上写出中国人在遭遇动荡时刻时的焦灼感。等这些人物写完了,我可能会着手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们都不要低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所具有的意义。如果光明、温暖的东西鼓舞过你们,我们应该传递给下一代人。
本文经合作方授权刊发。编辑:张瑶;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活动预告|许知远、罗新、吴琦、罗丹妮对谈:重新发现人
许知远新书旅行|所有人都是同代人
在时代入口找门的许知远
书写“走向世界”的梁启超
罗新对谈大头马:旅行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反思
许知远 × 吴琦 × 罗丹妮:编无法归类的书,做无法归类的人
梁启超的写作效率有多高
许知远:她是我心中的英雄
许知远中英文夹杂采访费翔真的很“装腔”
徐京坤 × 许知远:幸运会眷顾那些大胆的人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7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79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7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9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34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