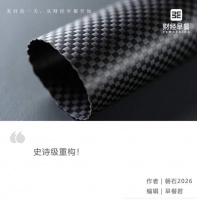陈东东:时光被我总结,秋气因回忆而聚拢
原标题:陈东东:时光被我总结,秋气因回忆而聚拢
陈东东四十年诗选《略多于悲哀:1981-2021》大致以诗歌体式编排,分短诗、组诗、长诗、地方诗与连行诗五辑,且内按写作时间为序,形成了一条生命与诗章之间共构并行的“动线”。所谓“动”即是“变”,主要体现在陈东东对语言(语体)的重构和再构上。当然,从写作的整体性而言,还可以说,陈东东正是尝试建构了一种稳定有序、向语言寻秘的“晶体”诗学,一切也就寓于不变之中。

陈东东,诗人,写作者,1961年生于上海,著有诗集《海神的一夜》(1981-2016短诗)、《星图与航迹》(1981-2016长诗)和诗文本《流水》等。
撰文 | 杨舒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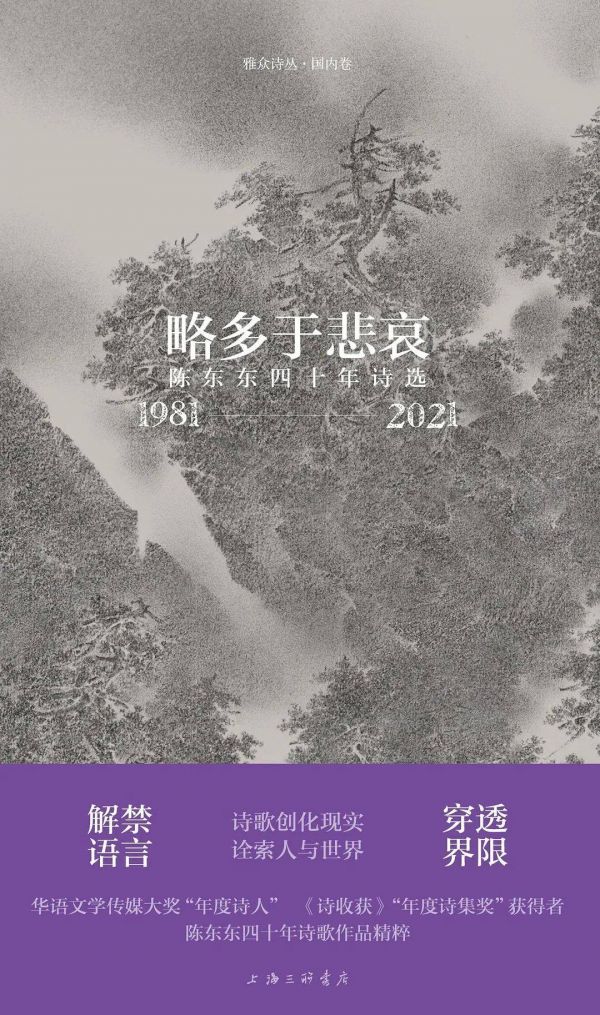
《略多于悲哀:陈东东四十年诗选 1981-2021》,作者:陈东东,版本: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2月
“晶体”何为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灵动地将诗人、作家划分成“火焰派”与“晶体派”两种不同风格类别,对此陈东东称,“我会毫不犹豫、心安理得、自然而然地站到晶体派旗下。”(《只言片语来自写作》)这里的“晶体”是指“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和能够折射光线”以及“特殊结构物的恒定”,以《看不见的城市》为例,每一章节即代表着“晶体”结构中的任意一面,而借数列、对称等形式整合起来看,又会发现其中具有精密、有序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文学中感性与理智的多维并存。同样,这一写作架构从陈东东的组诗《眼眶里的沙瞳仁》[拟少年行]细目便可一探:夜曲之一、夜曲之二、骑手、眼眶里的沙瞳仁、夜曲之三或马、成长的日子、骑手讲述的第一个故事、骑手讲述的第二个故事、去大海之路、一片荒凉、房舍、在我附近、海、骑手最后讲述的故事、沙漠或夜曲之四。每一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能联系紧密、完整合成一张少年行走的意识之网。
不过,如此显见的摹刻自然不是陈东东“晶体”诗学中的全部,具体至诗歌内容,更为直接的晶体形态在其早期诗作《语言》中就有出现,如“我的眼里,我的指缝间/食盐正闪闪发亮”,“食盐”既是热泪与透汗从“一个盛夏黄昏”处蒸发结成的晶体,也是浮于纸面、或隐匿眼中的“诗言”象征。另如“那些阴影投射/在旷野、海、干涸的河道、食盐的中午和每个人的腋窝之下/当一个夏季匆匆离去,我们看到/移居的宇航员在等待着倒数计时完毕/他高飞在我们的世界之上,能够真正把幻象认清”(《弹唱告知》)等,可以说,以食盐为代表,晶体在陈东东的诗中或可直观、或被虚化,但最终都指向了语言以及由语言所构成的思想和现实(超现实)。
相较列奥帕蒂等人对模糊的诗意的追求,晶体派则更为强调诗中词语表达的确切、以多重平面折射光线的能力,甚至“连确切性——都证明是双重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而如陈东东所言,“诗歌的魅力,在于无限虚构称之为幻象的真相之万象”,他的“晶体”诗学与其说是由“真相之万象”构成,又不如说是以语言之想象连接,尽管有时其对“模糊”与“无限”的区别也略为含混。但从诗人诗论谈起,并向“晶体”切问,也还尚可做到概观诗之一二——毕竟“晶体”何为更是陈东东多年以来冥思苦索的难题之一。维系自我语言生态即是陈东东“晶体”诗学中的内化逻辑,这一方面体现于诗中之城在现实与超现实、古典与现代精神间的多维构建,另一方面则反映为以“片断”入诗、将散文与诗复合关联的语体实验,诗的边界不断外延。

《海神的一夜》,作者:陈东东,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城与诗境的多维构建
陈东东祖籍江苏吴江,自1961年出生起便长期居住上海,20世纪80年代,他还是“海上”诗群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换言之,对于诗人来说,“南方或许是一个地域,但它却更是一个精神的向度”(《词的变奏》),无论如何下笔,都免不得它的明昧气韵,王东东在《大象的退却,或江南的对立面》中也称陈东东为“江南诗人”。这使得其诗长期以来总能保持语言格调上的一致。而参考此前海伦·文德勒对谢默斯·希尼诗中语法的分析,可认为,陈东东的诗也多属名词性质,正如他曾讲过的——“在名词之下,诗歌诞生了”(《词的变奏》)。不过,还必须同时意识到,他的诗又多以城市为叙述背景,综合来看,或可谓是先由名词构筑了一座文城,后因文城造就了一重诗境。但诗人对名词的多元选择也进而将城与诗境推向了多维的建构中去,如《应邀参观》一诗:“华灯从幽深处打开新境界”,古典情调与现代气质相随相生,在“镂花镜”“山海图”“青铜鹤鸟”和“YADDO”“电视机”等词的并行之际,陈东东还重构了一处第三空间:
谁要是
撩开它二十四小时热水蒸腾的雾气帷幕,
谁就会看到,绮窗外雪的戏剧
净化着,七个小矮人陶醉,更醉,
以他们的茫然追随漫卷的超现实公主……
这与前文“那晚上下雪,/桃花源被冰封藏进水晶罩……”近乎是同位、共时存在,而对童话的戏仿也混同了诗中本有的记忆与感知、现实与非现实,从而不得不以超现实的想象作为城的出口。整体而言,对多重语言的使用的确让陈东东的诗歌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均衡、和谐的“晶体”状态。
此外,在陈东东看来,俗世市民一直都生活在一座现实“二流的影子城市”里,只有“天国、乌托邦、移居外星的新人类村”才是城市的最高形式(《词的变奏》),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诗人对宇宙空间的持续探索密切关联;同时,城外城的设定也暗含了他对诗歌崇高性的追求,特别反映在组诗《即景与杂说》与《月全食》《宇航诗》《另一首宇航诗》等中。以《月全食》为例,“《逸周书》”和“卫星城”是展开此诗的双线,分别导引了“梳妆台镜”“长明灯”与“探测器”“宇航员”等两类名词,而作为“世界观对称的/两个方向”的象征,它们会同于陶渊明一句“此行谁使然?”,也让诗在重构语言中营造了一种超现实被禅意所裹藏的韵致。
自2017年起,陈东东还将自己“地方诗”的视域延至成都、东京、纽约等城,可以见得,在不同写作时期,江南文化中那种隐逸从容、不徐不疾的吴风古调也存在着明显的呈现差异。相较之下,此番对现实之城的突显更像是一重略有永恒回归意味的理想虚构,文末附注多对其所引诗句做出一定说明,如《成都》便是化用了李贺《相和歌辞·蜀国弦》与杜甫《蜀相》等。在这些城市诗中,陈东东用其文人式的眼光打量或真或假的历史过往,并与此前此地的诗人诗作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或可称是一次遥远的致敬),在诗里直接承续诗的古今。不过,古典美的愈来愈外化也同样限制了读者对于现实与超现实的想象余地,使诗在思想传达方面不断趋近于饱和,从而产生一种有距离的美感。这已与张枣等人在诗作中对中国古典传统所进行的现代转换有着明显区别。
综上,现实与超现实、古典与现代的多重语言叙述让陈东东的诗中之城呈现出一种多维的“晶体”结构,而在不同时期,诗风的稳中有变则多与他对南城古调的情感体认之差异相关,几方相峙与谋和对其诗作来说,更不失为是一种恒定的重复。

《我们时代的诗人》,作者:陈东东,版本: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4月
片断入诗的语体实验
陈东东曾回忆称,“有一次,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我打开灯,张枣在后面咯咯笑起来说‘陈点灯’,然后说他则被人唤作‘张镜中’。那首写于1984年秋天的《镜中》,被太多的人喜爱。我说我有点儿后悔写了《点灯》和《雨中的马》,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的印象里,像是被定格了。”(《我们时代的诗人》)如果从这本新诗选《略多于悲哀》开始读起,似乎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相比而言,陈东东此后的诗作语言稠密、意象繁复,与《点灯》《雨中的马》差异甚大,也如他所说,一直都在“设想、找寻和走通更具当代性的现代汉诗可能的路径”。而除意象、智识等语言内部流变之外,这一点还突出体现在了其以“片断”入诗、将散文与诗复合关联的语体实验上,同卡尔维诺对《看不见的城市》一书的表述相似,“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
以《十片断》为例,这首长篇连行诗共由“个人的记忆”“冬季”“树”“黎明”“城市之春”“在南方歌唱”“牺牲”“从诗篇里”“地理”“来世之书”十个部分构成,与前文提及的组诗《眼眶里的沙瞳仁》[拟少年行]在体式上何其相似,前后文义回绕,多面浑然一体。但其实,《十片断》还曾收录在陈东东1997年出版过的《词的变奏》中,那时他尚且称这是一种在“诗歌以外”的“诗人散文或诗人随笔”,《略多于悲哀》则将其归入“连行诗”一列,试图打破传统分行诗的外在形式,也显见了陈东东现如今将诗内化于文、诗话隐匿于诗的跨文体诗学观念,如其中《从诗篇里》一章:
时光被我总结。秋气因回忆而聚拢。刚刚偏离了舞蹈的群峰更向往热烈。闪电停留,在群峰之上,鹰一样的闪电要攫取季节酸涩的果实:
漆黑的粮仓
最后的风景
斑斓的锦鸡和
裸身于三枝火把的女性
从诗篇里,幻象和真理合而为一,仿佛首先跃出的老虎——以壮丽和盛大给了我恐惧……
而在另一首连行诗《一声》中,全诗仅由标号01至99共100句的“片断”构成,直接消解了原分行诗的固有体式,前后围绕声音与“元诗”话语产生一种绵延不断的、类似“晶体”空间有序又对称的链接效果,例如“01.需一行诗,一个词,甚至只需哇的一声,重新落实悬浮的世界。”与“98.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一生。”此外,后一句还明显是对鲁迅散文诗《秋夜》中“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的改写,如诗人所言,他在有意“为了写作而腾空文体”(《一声》)。
这种由“片断”入诗的语体实验,是陈东东对跨文体写作与“晶体”结构的追求之间的耦合表现。可以说,“晶体”在其诗作中既体现为对内部意象与语言表达的重构,又是片断与片断、诗与诗作之间思想情感的相互关联,同时还是宏观上包罗“万象”、诗与散文跨文体写作的尝试。能够理解,诗人对“晶体”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对绝对感性进行规避,这与艾伦·退特“要求诗既倚重内涵,又倚重外延”的“张力”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中“元诗”性的语言形式更像是陈东东对自己早期纯诗风格的延续(元诗与纯诗的关系,可参考王东东《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元诗观念》),这一“形而上学”倾向也与他提出的“诗人的自救和诗歌的自救”之需暗合。且“片断”入诗的写作方式又使他更进一步沉浸于“元诗”趣味之中,挑战了诗歌定义本身。而又如曾被卡尔维诺提名的另一位晶体派诗人瓦雷里所说,“需要做的是引导人们进入一个语言世界,它与用符号来交换行为或思想的普通体系毫不相干”(《文艺杂谈》),如果据此思考则可以认为,诗歌在写作的崇高性以外,可能还亟须达成它在语言(语体)重构、现实表达方面的自我平衡,这不仅仅是诗人陈东东的个人难题。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舒婷;编辑:张进;校对:陈荻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陈东东:时光被我总结,秋气因回忆而聚拢
每日一书|《略多于悲哀:陈东东四十年诗选》
时光机丨满满的回忆
谢霆锋在家追时光音乐会 因谭咏麟没邀请自己而生气
孙悦陈露怎么认识 因男篮总经理撮合而走到一起
琉球群岛自隋朝时被我国发现,明朝洪武五年归顺我国……
文咏珊坐地铁被我偶遇
头目: 可算被我抢到干杯了
早读丨“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
小物件重铸旧时光 80后手艺达人专注“复刻回忆”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7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596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49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