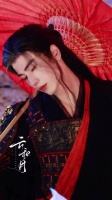钱颖一对话余隆∣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原标题:钱颖一对话余隆∣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有关科技、增长和未来趋势的洞见
在变化世界中保持企业创新活力的秘诀
艺术大师涵养创意和内驱动力的精神世界
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2011年到2018年任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期间举行的20场“院长对话”的实录,包括了一些当今世界知名度很高的创业家、企业家、投资家以及国内著名的人文艺术人士。
钱颖一对话余隆:
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2011年4月27日,余隆先生应邀与钱颖一教授在清华经管学院“人文日新沙龙”上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给我们讲述了开创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2011年4月27日,钱颖一与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左)在清华经管学院对话
钱颖一:你不仅自己境界已经到了,现在还试图使全国人民的境界都提高。你的名字是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连在一起,也同中国爱乐乐团连在一起,这是你大概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做的两件事。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余隆:坦率说,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你没有任何特别强的目的性的时候,就只有专业诉求。那个时候还是音乐节的早期,只是觉得像北京这么一个文化城市,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国际音乐节。当然我是搞音乐的,如果我搞美术的话,我就搞美术展去了。我认为北京需要这么一个国际化的活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就直接去做。一开始起点非常高,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逐步完成什么,我认为做事情就应该是一步到位。
当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至少理念要一步到位,明确要的是什么东西。
钱颖一:你当时想要的是什么?
余隆:必须是国际最高标准的音乐盛宴。
钱颖一:最高标准。
余隆:最高标准。所以北京音乐节从一开始。邀请来的艺术家都是世界级的、一流的。我们进行的工作都是开创性、划时代的工作:第一次引进瓦格纳全套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委约世界级的作曲家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把一些现代的作品展示在舞台上也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推动中国音乐家在全世界的作品展演,也是北京音乐节。不能功利,做事情完全凭着专业的知识去做,是会有好结果的。去年我们委约中国作曲家周龙写了一部《白蛇传》。
钱颖一:“委约”是什么?“委托”的“委”?在我们这里“违约”的意思是破坏合同。你说的是commission?
余隆:你说得对。上个礼拜接到通知,《白蛇传》拿到了普利策音乐奖。
钱颖一:那是最高的奖项。
余隆:当时这个作品拿奖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当时申请经费都没兴趣,因为是部现代作品,有的领导经常说:你们要委约一个作品的话,这个作品能不能成为《梁祝》和《黄河》?经常问这个问题,如果能成为传世作品就给钱。我说,还没写出来,怎么知道传不传世呢?说那得保证它是传世作品。我说那等于说我生一个儿子出来,我问这个儿子:你将来能不能哈佛的MBA毕业?要不能毕业,我就不给你吃饭。作品《梁祝》和《黄河》也是千百部作品淘汰下来、积累下来的,只有经过大量地创作,才能够有经典作品留下来。像《白蛇传》这个作品,当然是一个碰巧的事件,我们当时觉得,首先作曲家是可信任的,是一流的作曲家,是在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一个作曲家。第二,这部作品是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故事。第三,这部作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亮点,是由西方导演来导演中国的故事。
去年音乐节,我们有三部作品,一部叫《塞魅丽》,亨德尔的一部歌剧,是由一个中国导演导演的,中国导演眼里的西方歌剧;第二部是《白蛇传》,是西方导演眼里的中国歌剧;第三部叫《咏•别》,是中国导演眼里的中国的京剧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是,要从不同角度看到大家对文化视觉或者思想上的感觉。恰恰《白蛇传》得了普利策音乐奖,很多人现在回过头就觉得,当时为什么眼拙了,咱们没去参加。我说一句话,是考虑的视角问题,考虑的不是艺术,考虑是不是在市场上有结果。有的事情不完全是这么来的,艺术跟市场不一定完全能够画等号。
余隆生于上海,现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他是第一位应邀指挥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也是最早到中国来演奏的费城交响乐团的中国指挥家,与世界顶尖级交响乐团合作最多的华人指挥家。他于2010年11月获得中央音乐学院荣誉院士称号,是我国艺术家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钱颖一:太功利这个事儿,现在还是比较普遍,会伤害艺术。所以当时你不是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的。
余隆:做一件事情绝对不能从功利角度出发。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北京音乐节1998年开始第一届的时候,还比较简单,如果是今天的话,估计音乐节连建立都建立不起来。
钱颖一:那时候简单?
余隆:那时候还是简单。爱乐的情况不一样,音乐节更加民间一点,爱乐有一点官方背景的,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最好的交响乐团。我听说,那时候我们领导说,中国足球老踢不出去,乐团能不能出去?我就跟领导说,到今天为止我还说这句话:你把给中国足球的十分之一的钱给我的爱乐乐团的话,我何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乐团。
钱颖一:结果球没踢出去,乐团确实出去了,你前天刚从美国回来。
余隆:这个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乐乐团2009年被世界最权威的伦敦《留声机》(Gramophone)杂志评为世界上十个最优秀的、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之一。
钱颖一:这是很大的荣耀。
余隆:包括了伦敦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对乐团的评价不是说琴拉得好和坏的问题,是评判乐团对社会的影响力和责任有多大。中国爱乐乐团是作为唯一的亚洲乐团进去的,其他全是西方的。
钱颖一:那是非常厉害的。当时你接这个乐团的时候,咱们有不少乐团。
余隆:我不是接,我是参与创建这个乐团。我们在原来中国广播乐团的基础上,全部打散重新创建。
钱颖一:所以也是新的机制。
余隆:在当时算是,现在不能完全算是。
嘉宾合影
图源:北京国际音乐节
钱颖一:你刚才说的三部作品里面,你说你对文化互相的融合非常在意,你觉得这很重要,是吗?
余隆:我从来觉得,文化不应该被划分,我觉得没办法划分。很多人一定强调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应该是更加开放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更加开放了,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坐在下面的老师,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我们也有人出去,世界的交流,资讯的打开,根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划分得这么清楚。
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但说得稍微大一点,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化只能都属于全人类的。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区分到另外一个文化的对立面去。我曾经跟某位比较激进的同事一起开会,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入。我想问几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今天穿的衣服是中式的吗?发型也不是吧,你怎么不梳一辫子扎一鬏儿?第二个问题,我说:你今天来政协开我们这个会,开的宝马车来的,还是奥迪车来的?是骑头驴,还是坐车来的?今天的社会,大家应该有一个……
钱颖一:包容?
余隆:其实不单是包容,你得承认一个现实,我不愿意说“普世文化”这个词,但是的确是存在。像今天我们穿的衣服,没人再说是西装,大家可能说是正装。我们今天所有生活的用品已经不说只是中国或者美国的,或者德国的,是大家的,人类的,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文化上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大家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找到互相可以学习、借鉴的事情,这样的心态可能更好一点。如果到今天还这样,说应该抵御某个情况,尤其在文化界,再讲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我今天当然没有说划分界限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有包容性。
节选自《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北京国际音乐节延期举办 《千里江山图》走进古典音乐
北京国际音乐节25周年论坛在纽约举办,用音乐见证中国发展
中国爱乐乐团新乐季力推中国作品与世界对话交流
千里江山用交响乐绘出壮美河山
探寻体育电影使命!第18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产业论坛圆满举办
“从洛桑到北京”第十二届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开展
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论坛成功举办,在光影世界中感受体育魅力!
第18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发布暨公益联展启动活动圆满举办
北京深秋的故事 北京深秋的故事简介
关锦鹏监制新作《你记得,就好》北京国际电影节官宣 有望再创青春爱情电影标杆之作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7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0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