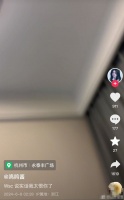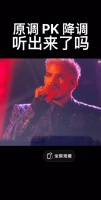口碑最佳!今年这部海影节佳作爆了

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于昨日落幕,本届“金椰奖”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获奖影片之一《桑格豪森的渴望》(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 / Phantoms of July),以其独特的情感质地成为本届最受影迷关注和喜爱的新作之一。德国导演尤利安·拉德迈耶(Julian Radlmaier)在过去十余年间,以对历史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先锋电影传统的不断重写,构建了属于当代德国电影的独特思想路径。尤利安的长期合作伙伴、制片人基里尔·克拉索夫斯基(Kirill Krasovski)亦在每一次美学实验中同行,为其作品赋予了创作动力。影片女主角克拉拉·施温宁(Clara Schwinning)因上一部作品《一个美丽的地方》在2023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得当代电影人单元金豹奖最佳女演员,是德国新生代演员的亮眼面孔。
当代德国电影研究者张超群(下简称RC张)对三位主创(简称尤利安、克拉拉与基里尔)进行了万字深度访谈。谈话从“渴望”(Sehnsucht)的多重传统与德国本土小镇桑格豪森(Sangehausen)开始,延伸至幽灵、移民、托洛茨基、诺瓦利斯,与爱森斯坦未竟的《资本论》计划,逐步揭开影片背后复杂的思想,以及系统回顾了尤利安幽默而颇具思想性的整体创作脉络。

“渴望”(Sehnsucht)的修辞:德国浪漫主义与流行文化
RC张:在片名 《桑格豪森的渴望》(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 中,“Sehnsucht” 是一个极具德语文化特性的、几乎无法被准确翻译的词;而国际英文片名 Phantoms of July 又指向略微不同、更加幽灵般的意象。2006 年,瓦莱斯卡·格里策巴赫也拍过一部名为《渴望》(Sehnsucht)的电影,同样发生在德国东部,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尤利安:所以,是的,我知道那部片子。瓦莱斯卡她也算是柏林学派的导演,也在DFFB教书。我对她有点了解。那部名为《渴望》的电影我也知道,因为我开始拍电影大概就是2006年左右,我那时搬到柏林开始学电影。当时这些电影正好在电影院里放映,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到的。
RC 张:你在这些电影中想追寻的是什么样的“Sehnsucht”,以及它和那种纯粹浪漫或怀旧式的向往有什么不同?
尤利安: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是自然而然地从不同的因素中产生的。首先,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拍一部关于“Sehnsucht”的电影,这并不是最初的想法。只是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塑造的那些角色慢慢开始有了一种渴望的情绪。然后当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很快发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其实就是在靠近桑格豪森的一个小镇出生的,而他正是你在德国会想到的最能谈论“Sehnsucht”这个主题的作家。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很清楚这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主题。这样一来,我之前写的内容和这种来自地理背景的联系就自然融合了。
另外我并不是在特意想着瓦莱斯卡的那部《渴望》,因为“Sehnsucht”这个概念在德国本身就很常见,也很有名,并不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主题。我之所以喜欢用“Sehnsucht in Sangerhausen”这个片名,是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有那种略微通俗、流行歌的质感,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在这个词里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含义。在更严肃的层面上,我觉得它也许关乎一种德国政治上的渴望,比如对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渴望,对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的渴望,或者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的向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更经典、更浪漫的感觉,就是想象有另一种生活存在,而不必具体去定义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流行音乐里也常常有这种意味。我觉得有趣的是,虽然“Sehnsucht”这个词可能有点听起来很通俗、很“廉价”的流行意味,但它其实内在有一种政治潜力。这种很普遍的“我想去别处”的渴望其实隐藏着一种对现有德国社会结构的不满和对更好生活的想象。当然,我并不认为一切都能靠政治解决,那太天真了,但我喜欢的是,这个词里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层面,它能把这些不同层次的情感和想法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我当时想的还有一点是,我可能也想通过这部电影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之前的那些影片更像是有一种模式化的、带有布莱希特风格的结构,或者说更系统化、更有模型感的结构。在那些电影里,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感受虽然有出现,但并不是那么重要。而这一次我更想探索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情感,并看看这些个人情感如何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RC 张:为什么影片的国际片名没有延续这种渴望,而是用的是“phantoms”(幽灵)?
尤利安:然后关于“Phantoms”这个名字的问题,就像你提到的,这个词很难翻译。在不同国家你都得找一个新的翻译方式。而且另一个问题是“桑格豪森”这个地名太不为人所知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所以这有点像是一种妥协。发行方和销售公司都说这个片名在国际上会很难让人有共鸣,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觉得“Phantoms of July”这个折中方案还可以接受,虽然有点遗憾,因为它失去了原本德语片名里那种明确的地理指涉,而且我喜欢德语片名中“Sehnsucht”一开始就让你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也许在英语里你找的是“幽灵”,而不是某种情感。但我喜欢这个对比:七月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月份,一切都成熟了,而“幽灵”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且七月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月份,所以也许这些“七月的幽灵”有某种有趣的层次。
RC 张:“在你看来,‘Sehnsucht’和‘Heimat’是不同的吗?有一些论断是这两种情感可能类似。但在看了你的电影之后,我觉得‘Heimat’并不是那样的概念,对吧?
尤利安: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其实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德国浪漫主义的那一部分。那种浪漫主义在历史上最后变成了某种围绕德国本身的东西——就像是为国家、为德国灵魂而存在的‘Sehnsucht’。而我的想法是想把这种情感和浪漫主义从这种非常德国化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让它对所有人都开放,无论是移民、韩国人、伊朗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不是只局限于德国灵魂的概念。这样一来,它就更国际化了。
从文本到地方:全新的创作路径
RC 张:您之前的作品,如《吸血鬼》(Blutsauger)或《一只市民阶级犬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of a Bourgeois Dog),与历史文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苏联文学和先锋作品有着紧密联系。而这次是您第一次从一个“地方”出发进行创作。您会如何描述这种转变?与从理论与档案出发相比,从桑格豪森这一地点出发为您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
尤利安:是的,没错。我当时觉得我之前的那种工作方式好像已经走到头了。我感觉自己要么就开始自我模仿、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并越做越糟,要么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路径。我真的很想做出改变。所以就像你说的,以前我常常是从文本、非常抽象的概念出发,然后在现实中寻找与这些抽象概念对应的东西。而这次我反过来了,我从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小镇开始。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一种从物质到概念的路径。以前我是从理想的概念出发,现在则是从具体的物质现实开始,然后再上升到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对观众来说也更真实。当然,后来还是会有一些文学引用,比如我们提到的诺瓦利斯的“蓝花”,但这些引用是更自然地在后期出现的。我仍然对理论和理论问题感兴趣,但这次它们更像是用来反思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一开始的出发点。
RC 张:与此同时,在创作过程中,这座城市是否曾“纠正”或重塑过您最初的剧本构想?这个小镇是否从一开始就重塑了剧本呢?
尤利安:是的,完全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在我来到这个小镇之前根本没有剧本。整件事就是从我来到这里开始的,然后它不断地演变。基本上,我先来到这个小镇,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我看到的第一批人是女服务员,我就在想:在这样一个小镇里,一个女服务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想,我是从柏林来的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和这里的一个女服务员见面会怎样?接着我注意到附近有音乐会的场地,我想也许他们可以是音乐家之类的。就这样,一切开始成型。我还想起了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的电影《金发女郎的爱情》(Lásky jedné plavovlásky,1965),讲的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女人爱上音乐家的故事。我想也许这里也可以有点类似的故事。然后在晚上,我去了另一家披萨店,注意到那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来自北马其顿,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走在镇上时,我还看到有来自阿富汗的难民,还有越南移民在这里生活。这让我意识到,很多德国关于东德的电影根本不呈现这些移民的存在,好像移民完全不存在一样。即使在佩措尔德的电影里,你也几乎看不到任何非德国人。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这根本不是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RC 张:在看这部电影时,我对桑格豪森城中的那些雕像、纪念碑和公共雕塑特别有感触。它们似乎不仅是背景,而像是一种被重新“引用”的现成文本,带着当地历史、政治与审美的痕迹。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把这些雕像当作一种新的“引用系统”,去替代以往作品中来自文学或理论文本的引用?
尤利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如今已经不再拥有原先的工业,整个产业已经消失,经济也因此陷入了衰退,失业率高企,人们也因此感到被羞辱。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雕像仿佛在提醒我们那段曾经辉煌的工人历史,它们带有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感,仿佛过去仍然在当下回荡。这些雕像并不是在颂扬那些“美好旧时光”,而是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痕迹仍然存在于当下。

重写德国现实:移民与原东德日常生活的幽灵
RC张:你把拍摄放在了前东德地区,而且我注意到片中人物的母亲曾在DEFA负责胶片材料的工厂工作。这样的设置出于怎样的考量?
尤利安:是的,在桑格豪森附近曾经有一家工厂,名叫ORWO胶片厂(East German Film Stock Manufacturer),负责专门生产胶片材料,这些胶片被非常广泛地使用。我不确定它是否出口到苏联,但它确实为很多国家生产胶片原料。有一本关于这家工厂的书非常好看,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而且当时这项工作仍然高度依赖手工。读到这些女性如何熟练掌握自己的工作,并对制作胶片这种劳动产生一种自豪感,非常有趣。我们这部电影用的也是胶片拍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向她们致意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另一个层面——很多参与项目的音乐人来自西德,他们对东德电影文化完全不了解。
所以这个设置其实有两层意义。比如乌苏拉的父亲开玩笑说,东德电影之所以好,是因为母亲的化学和胶片技术好。我很喜欢这种带有工人阶级视角的电影观,因为电影背后总有人在生产材料:不只有导演和摄影师,这些劳动者也应该被看到。后来片中提到一位女演员,但西德来的人甚至不知道她是谁。这样也暗示了今天的现实:这段文化历史几乎无人知晓,而西德人对东德文化几乎没有兴趣。
RC张:这部电影是否受到苏联或东欧阵营电影的影响?
尤利安:是的,当然有。其实有一个影响我们之前没提到,那就是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的《漫长的告别》(1971)。我们特别关注她如何使用摄影机——她的调度、运动、变焦和平摇——令人着迷的是,她只需非常少的手段:摄影机甚至可以固定不动,但通过变焦和平移,她依然能创造极为复杂的视觉语言。我们非常欣赏她影片中这种做法——在同一个镜头内从特写过渡到大全景,通过运动制造惊喜、节奏和情绪变化。这种处理方式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参考的另一个作品是乌兹别克斯坦导演埃里耶尔·伊什穆哈梅多夫 (Elyer Ishmukhamedov) 的《温柔》(1967)。它是一部非常美的电影,我们也特别喜欢这部片的摄影语言,可以说,嗯,我们确实也从里面“偷”了点东西。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乌兹别克电影非常精彩,但伊什穆哈梅多夫的名字太难记了,我总是记不住,而《温柔》确实非常值得观看——我强烈推荐。
RC张:我发现您很多电影在章节切换前音乐会明显变化,而且常带有一种非常德国式、交响乐般的气质。感觉影片几乎是由音乐构成的。您是如何选择这些音乐的?它们是否带有某种隐喻意义?
尤利安:在这部电影里,音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用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尤其是罗伯特·舒曼,他也来自东德、来自这个地区。但更重要的不是地域,而是我非常喜欢那首钢琴曲的纯真气质。它叫《异国与异国人们》 (Von fremden Ländern und Menschen) ,是舒曼《童年情景》(Kinderszenen)的开篇。它像一个孩子在幻想远方、陌生的人以及另一种世界——我觉得这种气息非常适合这部电影。它简单,却拥有深沉的情感,我非常喜欢这种平衡感。
同时,为了与这种“高雅德国艺术”、古典音乐形成对比,我也想要一些有类似情绪但形式不同的流行歌曲。我们在当地发现了真实存在的民谣,甚至是关于我们拍摄的那个小镇的歌曲,然后我们就把它们收集起来。我觉得这种对照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这种处理方式。后来,我直觉上觉得需要一些更神秘的声音。我想到长笛,因为在童话里,长笛往往象征魔法,像是在召唤你去某个地方。我偶然听到日本作曲家武满彻(Tōru Takemitsu)的一首曲子,觉得非常契合。一开始我还担心,我对这种音乐到底了解多少?它在这里有意义吗?但后来我发现他还有另一首我们用了的作品,那是一首吉他曲,竟然是《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的浪漫化改编。那一刻我就觉得——他就是这部电影的正确作曲者:能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歌曲转化为抒情浪漫的音乐的人。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处理,尤其是因为《国际歌》几乎出现在我所有电影里,而这次它以浪漫吉他版本回归。
表演与现实相遇:克拉拉的乌苏拉与裸男
RC张:克拉拉,我觉得你在这部电影中的存在非常特别,你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我想问问你这次的拍摄体验如何?你的前作中有不少非职业演员,这次的合作感受怎样?
克拉拉:在桑格豪森里确实很特别,因为我们和真正住在当地的人一起工作,他们也出现在电影里。我记得我们在桑格豪森排练,比如电影里卖冰淇淋和薯条的人、我在旅馆里问路的那个人,甚至我饰演角色的邻居——他们都是真的来自那里。所以当我读剧本,再走进片中人物生活的环境时,看到剧本通过他们变成具体的人和情境,非常美妙——他们演的正是他们生活的世界,特别契合。当然我们也和职业演员合作,我觉得这种混合让现场氛围非常好。对我们演员来说,这特别好,因为你不需要“演”很多——你就在真实的互动里自然回应。
RC张:我也想问问你与那位韩国演员合作的感觉,但他常出现在尤利安的电影里。你能分享一下与他和孙子一起表演的经历吗?在电影中我感受到一种非常温暖的氛围,特别迷人,这样的组合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
克拉拉:真的非常美好。那位年长的韩国演员Kyung-Taek Lie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有时候对他来说体力上会有点挑战,比如我们爬山时,因为他大概七十岁左右,但他每天到片场都带着自信的能量,对我们充满好奇,什么事都不会让他烦躁,总是说:“我们怎么来完成它?”而他的孙子,他在片中的角色叫Buk,但那其实就是他的真名。他非常可爱,也很聪明。因为是孩子,他每天只能在片场待几小时,但他能准确理解自己要做什么,这真的很惊人,他学得非常快。
尤利安:我想补充一点,我对这部电影里的表演过程真的很满意。过去的作品中,我往往主要与职业演员合作,而且每一部电影里职业演员的比例都在增加。但我觉得,当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相遇时,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职业演员必须去回应真实的人,而反过来,他们也会帮助非职业演员——他们会创造一种氛围,像是在说:“现在我们在表演,这是属于表演的空间。” 这种相互作用非常好。它也产生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说话节奏。当然也有局限,但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我们真正达到了“最佳组合”:既利用了非职业演员的魅力,同时又能与职业演员一起深入工作,创造那些只有受过训练的演员才能做到的精确瞬间——这些都是通过长时间排练和细致打磨实现的。对我来说,这次真的是“两全其美”,我非常满意。
RC张:那你们下一部电影还会合作吗?
尤利安:我希望如此。这是一次很棒的创作过程——为什么不继续呢?
克拉拉:我补充一下前面的问题,那个穿西装的酒店工作人员,其实在片场非常紧张。他一直在发抖,甚至紧张到吃不下东西。这件事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特别的。对我们来说,拍电影是一种日常,有时会很辛苦,有时又很奇妙。但看到有人因为参与而如此紧张,就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团队聚在一起创作,其实意义很大。
RC张:你是如何决定设置那两个裸男的情节的?
尤利安:这很有趣,这是我们在中国被问得最多的问题。观众每次看到那两个裸男都特别开心、全场大笑。其实在德国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叫 FKK(Freikörperkultur,自由身体文化/自然主义/天体运动),从 20 世纪早期就存在,尤其在东德发展得特别强。比如在桑格豪森附近,真的有官方标注的“裸身徒步路线”——地图上清清楚楚写着“裸体徒步道”,在哈尔茨山区非常常见。所以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文化。
RC张:我知道德国有很多裸海滩。
尤利安:是的,那也是东德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也变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东德人喜欢光着身子。”所以我不想让东德人来演那两个裸男,而是让巴伐利亚人来演,因为我是巴伐利亚人。如果我要开这个玩笑,我宁愿把笑话开在我自己的故乡,而不是再去强化关于东德的刻板印象。
RC张:我想到《Go Trabi Go》这部统一后爆火的喜剧,里面一家人穿越德国去意大利,沿途看到很多裸奔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东德的陈词滥调。
尤利安:对,我知道那部影片。而且很多东德人非常不喜欢它,因为它不断消费和嘲弄关于东德的陈词滥调。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作为来自西德的人,如何在不伤害当地文化的前提下处理这些元素?我们的方式是平衡,我们也有裸男,但他们来自巴伐利亚。这样笑话不是强加在拍摄地的人身上。但这场戏不仅是搞笑的,这两个男人也带着一种侵略性的、不舒服的男性气质:靠近、触碰、有些有毒,我们更多想传达的是这种男性存在,而不是裸体本身。最有趣的是演员本人的贡献。他在试镜录像里拉手风琴,我们聊的时候他说:“剧本里没有音乐,也许我可以演奏点什么。”随后又说:“舒伯特为一些‘反暴力’的诗写过曲子,也许我可以弹类似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于是音乐成了那场戏完美的异质层次。
RC张:你在片中刻意选择非德国产的汽车吗?因为我注意到片里出现了很多韩国现代汽车,只有韩国人开大众,而且最后他还把那辆车卖掉了。
尤利安: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老实说,我们只是用了桑格豪森当地能找到的车。但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应该装作是有意的,但其实没有,我真的没想那么多。确实,这里有最好笑的一点:片中的那个车行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名字真的叫 “Wolf 汽车行”,但这完全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店真的叫这个。更荒诞的是:
我根本不懂车。我看到车标上有一个 H 就以为是本田(Honda),拍对白时演员也说“本田”。结果在后期混音时,有人说:“那不是 Honda ——是Hyundai(现代)。”于是声音师必须回到对白录音里,去找一个“e”的元音,然后剪音节拼接成Hyundai。光改这个品牌名他就花了20分钟。电影制作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谬。
基里尔:当我把影院的截图发出去后,就像命运式的报复或巧合一样,一分钟后我们突然多了一个来自桑格豪森的新关注者。感觉像是当地人亲自确认我们把现代说错了。片中的车行并非沃尔夫斯堡或大众集团相关,而是真的叫“Wolf 汽车行”,因为老板姓Wolf。
RC张:为什么你在电影里围绕德语字母“U(wu)”做了那么多笑话?
尤利安:对我来说,写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东西。有时候我说出来都觉得有点害羞,尤其在制片人面前,因为我通常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好点子。有些人脑子里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概念,但我不是。我通常从一个有点蠢的想法开始,然后不断改,直到它变好一点。电影里的 “U” 就是这样来的。写那个场景时,我突然注意到可以插一个 “U”,于是我想:那能不能再多放几个?结果整场戏就从这里发展起来了。有时你从一个傻想法开始,然后去 Google 一下,却发现了新东西。比如我搜有没有一个元素叫“Uue”,结果真的有 ——更有趣的是,那个元素的寿命非常短,会迅速消失。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和“关系短暂”的笑话建立连接。这就是我喜欢写作的原因——当你保持开放时,偶然出现的东西会塑造你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跟拍电影很像:你得保持感受力,去观察、收集那些现实中偶然撞到你的东西。现实往往比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更有创意。

影像思想的传递:DFFB与新的德国电影方法
RC张:您和许多长期合作的导演都曾在 DFFB 学习,我好奇这所学校在个人或职业上对您有什么影响?能否分享一些经历?
尤利安:对我来说,DFFB在多个层面都非常重要。我读书期间,学校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刚入学时制度仍然完整,但不久校长更换,许多教师被解雇、也有人因为不满而离开,所以学校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早期学习中,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老师Martin Martschewski对我影响很大。他有纪录片背景,会放非常有意思的片子。他常说,电影应该像在森林中散步:你走到拐角,突然看到新的东西。电影没有必要是线性叙事,它可以像漫步那样展开。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我,我想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同学。但最重要的其实是其他学生,比如我的制片人基里尔,我们合作至今已有十五年左右;还有亚历山大·科贝里泽(Aleksandre Koberidze),我们在同一个导演班。他原本先读了制片一年,后来转导演,所以重修一年,我们才在同班相遇。班上还有来自瑞士的双胞胎导演拉蒙·曲尔歇尔(Ramon Zürcher)和西尔万·曲尔歇尔(Silvan Zürcher),他们也和我们同届。马克斯·林兹(Max Linz)早我一年入学,但我早就认识他,因为我们曾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FU Berlin)一起学电影理论。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是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葛德鲁特·柯赫(Gertrud Koch),她来自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德国最早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之一,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林茨申请DFFB时,我意识到:既然我认识的人都能申请,那也许我也可以试试,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电影背景。
RC张:那DFFB授予正式文凭吗?
尤利安:是的,它没有学位证。所以如果我们停止拍片,在保险体系里会遇到问题。但本片的伊朗摄影师Faraz Fesharaki也在那学习,所以我们至今还与学校里的人紧密合作——那段经历极其重要。
RC张:您本科读的是电影理论,我觉得这也让您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学术性?
尤利安:我不确定那是好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的“诅咒”。我有学术情结,总在想“教授会怎么想?”我曾作为理论文本的翻译与编辑参与工作,包括一门处理法国哲学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译作的重要课程。还有我的朋友 Kyung-Taek Lie,他总演我电影里的普通人角色。他的儿子Sulgi Lie也是电影学者。他的新书“Comes Walking. Adorno’s Slapstick: Charlie Chaplin & The Marx Brothers”写得很好。通过他们,我觉得自己仍然与电影理论保持联系。
RC张: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对你有影响吗?
尤利安:严格来说,并不是非常直接或强烈。但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学习时,我们感觉学校,或者说行业和资助体系的一部分,期待我们去做更接近商业电影的东西。不是完全好莱坞式,但那种模仿商业审美的倾向是存在的。于是我们开始回头看前几届 DFFB 学生拍过什么。我觉得与像法罗基这样的人接触,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信心,即电影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手段去做也依然很有趣。因为很多电影学生都想拍一个五分钟的短片,却让它看起来像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制作,而这种企图往往注定失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简洁没问题,想法比制作规模更重要,而电影也可以具有某种散文式、思想性的品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幽灵的回返:托洛茨基与《资本论》
RC 张:我也想到爱森斯坦本人曾试图拍摄《资本论》,但这个计划既雄心勃勃,又最终未能完成。您在过往的多部电影中始终引用《资本论》,这一系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是一种对资本论项目的延续?因为在《吸血鬼》中,饰演托洛茨基的那个角色,他逃到了德国城市,这个选择非常引人入胜,立刻让我想起了爱森斯坦未完成的《资本论》尝试。
尤利安: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轶事,我曾听说在《十月》这部影片中,原本有托洛茨基的戏份,不过后来爱森斯坦不得不将托洛茨基的部分剪掉。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太确定,我在不同的资料中看到过不同的说法。我同时曾在某本影史书籍中读到,爱森斯坦当时为托洛茨基选角的那位演员,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是一位牙医,或者说类似牙医的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趣,一个现实中的牙医竟然成了银幕上的托洛茨基,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爱森斯坦经常启用非专业演员,我也很好奇这位演员到底是谁。这个好奇心就是我最初的动机。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部由伊利亚·埃伦堡(Ilya Ehrenburg)所著的小说,他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著名的苏联作家。埃伦堡曾创造了“解冻期”这一概念。在他的其中一本有趣的作品《弗拉西克·赫罗伊茨万斯的生活》中,这本书写于二十年代,对于当时的苏联环境而言,这部作品有些不太符合当时的规定,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二十年代面对一个宣言时打了个喷嚏,被人问及为何打喷嚏,他因此吓得逃离了,最后来到了德国,在电影拍摄现场出现。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在讽刺弗里茨·朗的电影,我因此得到了灵感,觉得这和我想要表达的情节有相似之处。接着我想,如果在二十年代,有人从苏联乘船去美国,途中可能会在德国停留,而当时的船只往往会沿着波罗的海沿岸航行,而那个年代,茂瑙也正在拍摄《诺斯费拉图》。于是我就想象,或许这部电影会是爱森斯坦与茂瑙相遇的一个场景,像是《十月》与《诺斯费拉图》的交汇,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混合,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构思。
RC 张:在你的电影中,你是否曾尝试“将《资本论》视觉化”?你有过这样的意图吗?
尤利安:其实没有,因为我认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实话,我也不确定那样的东西到底会不会真正吸引我。我尊敬爱森斯坦,但我也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愿意观看一部《资本论》的电影改编。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智慧有限、会困惑、也会迷惘的人,我究竟如何与这一理论建立联系。它关乎的其实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一个具象的人怎样与理论相遇”。理论有时能帮助我们,但也可能让我们更加困惑。因此我更关注的是这种个人化的关系。
作为新的思考的幽默:基里尔的制片与非讽刺的姿态
RC张:基里尔,你和尤利安合作多年,应该算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你们之间形成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在项目发展过程中,你的意见会影响到作品走向吗?
基里尔:其实你永远不知道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我们经常讨论,但很少会有“这个主意是你给的”“那个是我定的”的时刻。昨天觉得重要的东西,今天可能已经不相关了。这就是创作过程。我们交流、提供意见,但这不是“制片主导”的电影,这是尤利安的电影,他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尤利安:是的,但有时候他确实是必要的合作伙伴。当然,这取决于你问谁,但基里尔经常提出很有趣的点子。我们聊天时,东西就逐渐成形了。哪些想法有共鸣,哪些没有,你能立刻感觉到。而这种过程只能发生在你信任的人身上;如果跟不信任的人做这个,创作反而会被毁掉。
基里尔:没错。如果你听一百个人的意见,你就会把项目杀死。你需要专注于几个真正有用的声音。我们的讨论价值就在于交换想法:设定、主题、可能的情节、什么有趣、什么无聊。不需要深入细节,只是看看哪些东西能点亮你的大脑。
尤利安:比如那两个裸男,基里尔听到后笑得特别开心,那我就知道这个笑话应该留在剧本里。如果没人笑,它可能就被删掉了。这部电影其实也有很具体的一面:基里尔建议我可以在这个地区做项目,因为他刚好在那里成立了公司。一开始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但后来我开始查资料、探索这个地区,最终发现了这个城市,于是项目诞生了。电影有时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就像爱森斯坦拍《十月》可能是因为当时正逢革命周年,有人对他说“如果拍十月革命你会得到支持”。电影创作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运作的。
基里尔:对,那一次讨论并不是“你必须在这里写剧本”,只是一个邀请:这里有资源、有支持,或许我们能比上一部更快推进,项目规模也可以小一些,不用花五年筹资。
RC张:你现在还会为资金所困吗?
尤利安:我当然没有真的在苹果种植园工作,但有时候感觉差不多就是那样。我曾经拿到了一个新的写作资助,如果没拿到,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安全保障。我们做的电影也赚不了钱。所以一直都是,怎么说呢,像从一个收成熬到下一个收成一样。当然我不是字面意义上去摘苹果,我的意思是:作为独立电影人,我们没有安全感。如果这个写作资助没批下来,我可能不会真的去摘苹果,但感受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在项目之间挣扎,寄希望于事情能顺利发生。如果没发生,就得去找别的工作,任何能糊口的工作。
RC张:你在很多影片中都使用幽默。你认为幽默或喜剧可以是一种特别的姿态吗?
尤利安:这个问题我常被问,但我从没有一个完美答案。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讽刺。讽刺常常调侃的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它更像网络meme:有效,但不具变革性。我喜欢的幽默更像是一种生成新的思考的幽默,或者像卓别林那样,让弱者拥有对强者的反击力量的幽默:一种更谦逊、更人的幽默。幽默本身是否是政治的,我不确定,但作为创作者和观众,我感觉幽默能创造一种平视的交流。当理论和政治太宏大、沉重、令人畏惧时,幽默让它变得可被接近。有时幽默也是思考的标志:当我觉得某件事好笑时,其实是因为那一刻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然我不会意识到它好笑。对我来说,幽默常常来自把两个不通常连接的事物连接起来,而我喜欢这种意外的连接。这可能不是最清晰的回答,但也许还能表达出一些东西。


相关知识
观影心得分享 口碑佳作推荐
从“东莞腊肠”到“反骨琪”,今年TVB的最佳女配角是她了?
这部创造口碑和票房奇迹的悬疑佳作十周年啦
海一天获北影节天坛奖最佳男配角,马丽感动落泪
肖战新作《藏海传》圆满杀青,众多明星齐聚一堂,共同期待成为爆款佳作
《一雪前耻》 千万不要错过这部佳作 一起观影 因一段情节看完全剧 好片推荐
口碑票房双爆,年度最好的人气温情喜剧来啦
最佳男配角是双黄蛋
《捕风追影》成近十年最佳动作片,成龙这一次没有令人失望!
第三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提名揭晓,雷佳音黄志忠等角逐最佳男主角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335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849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929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9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95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812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87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293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225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