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能够拯救女性”
原标题:“这本书能够拯救女性”

栏目主持丨庞晔
海报丨史昌鹏
排版丨二水
支持|白话日报&濛仔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是日本女性主义先驱上野千鹤子与人气作家铃木凉美历时一年的通信。两位年龄相差35岁、走过迥异人生的女性围绕恋爱、婚姻和工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刻地讨论。
上野千鹤子出生于1948年,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铃木凉美是日本畅销书作家,曾经担任经济记者、成人电影演员。
分享人周胡桃对本书提出了七个问题,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01
挣脱“受害者”这一身份,是许多性骚扰受害者/性工作者长时间的态度。她们为什么不愿称自己为“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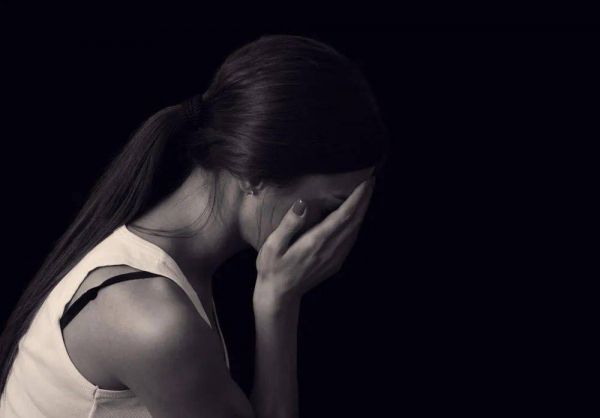
答:正如上野千鹤子在阅读铃木凉美关于成人电影女演员的硕士毕业论文时的感受,原文采用了微妙的局外人视角,透露出为自己开脱的态度,传达出一种“这不是我”的信号。长时间以来,铃木凉美一直试图挣脱“受害者”一词织成的牢笼,作为性工作者,她曾认为“被践踏者”的标签会让自己变得无趣、庸常、碍事、软弱,还会招致旁人的怜悯。
然而,2019年势头强劲的#KuToo运动(日本职场女性抗议工作场合强制要求女性穿高跟鞋的运动)传达的女性“不畏惧当受害者”的态度让铃木凉美着实震撼。是接纳受害者之名,还是不甘如此?上野千鹤子在回信中回答了她的问题。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被贴上软弱的标签,这种心态叫做“恐弱”。这也是精英女性经常陷入的一种心态。恐弱是因为自己身上也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会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这是铃木凉美长期拒绝“受害者”这一身份标签的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铃木凉美在《始于极限》中问道:“女性无法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是否会妨碍女性运动?”“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变化,‘勇于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成为了一种更加先锋的态度,”上野千鹤子在回信中解答道:“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性工作者强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愿选择)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目的则是通过强调女性的自主性为男性的做法免责。”对女性而言,性工作是一种经济行为,男性作为支付酬劳的消费者,他们到底在买什么?他们从心底深知女性的身体不应该是商品,那不是应该用钱买的东西,于是把这份亏心转嫁给了对面的女性,他们最有力的借口就是女性的“自我决定”。
女性拒绝接纳“受害者”的标签是否影响女性运动的进步?这一问题是社会学领域经典的“结构”与“主体”的矛盾。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从这种结构中获利,但长远看,却不利于结构的优化。
#02
“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上野千鹤子这样评价道。对比略显单纯的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为什么复杂又激烈得多?

答:“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这是上野千鹤子对铃木凉美和她母亲的关系的评价。铃木凉美的母亲是在她身处的时代中少有的聪慧又独立的女性。出身于优渥的家庭,获得了优秀的学历,在跨国企业做体面的工作,成为家庭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丈夫则承担了主要的抚育义务,是当时少有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母亲在铃木凉美的眼里是“看似合理但背负矛盾”的存在。铃木凉美批判道,自己的母亲厌恶用“女人味”做生意的人,却异常地外表至上主义:当上大学老师后,花一周的时间拍摄讲课用的讲师资料照片,如果得不到“美女”的评价,宁肯不抛头露面。她似乎把“做一个吸引男性的女人”看得比什么都有价值,却在内心里瞧不起那些公然将之兑换成金钱的女人。
上野千鹤子犀利地指出,从未有过经济压力的铃木凉美涉足性产业的理由之一就是想成为母亲无法理解的对象,做母亲最厌恶的“那一行”。同为女性,共享太多重叠的经历,母亲的聪慧意味着“妈妈了解你的一切”,于是,女儿失去了喘息的空间,无路可逃,无处可躲。上野千鹤子说,孩子长大成人,意味着“孩子内心怀揣了父母不了解的阴暗面”。为了精准地攻击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原指希腊神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代指唯一的弱点),铃木凉美选择了步入夜世界,彻底成为母亲无法理解的“利用身体和美色交换金钱”的女性。
出生于不同的时代,母女二人却分享着同为女性所面对的困顿与纠结,其中的互相理解与爱,伴随着微妙的嫉妒与指责。这是母女关系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03
女性对男性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放弃与男性对话?

答:网络上流行一句话:“这世界上最大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男人的本质之后依然坚持异性恋。”这句话改编自罗曼·罗兰那句著名的话。
随着对女性主义的探讨更为多元和开放,许多女性经常表示对男性感到失望,铃木凉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之一。在《始于极限》中,她曾多次就个人的经历阐述她对男性“失望透顶”的原因。铃木凉美对男人的印象停留在年轻时从事成人行业的经历。她因此对男性灰心失望,丧失了与他们沟通的希望,觉得“对这群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在对男性失望透顶的情况下,如何不放弃与男性认真地对话呢?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回答了铃木凉美的疑问。说“男性没救了”或“女性没救了”这样的话是亵渎的,因为这和直接说“人类都没救了”是一样武断和片面的。作为个体,人有可能是可悲滑稽的,也有可能是崇高伟大的。虽然统计数据似乎传达了“男人没救了”的信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
上野千鹤子提到心理学家霜山德尔,他留下“自灯明”这三个字,意思是:在黑暗中行走,依靠微弱的光照亮自己的脚下。上野千鹤子说,光是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他们这样品格高尚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走一遭。不对男性绝望,是因为上野千鹤子曾经遇到过值得相信的人,与这些人的关系,带出了她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引出恶意,善意会得到些许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生揣摩上意和阿谀奉承,无知会催生傲慢与自大。也许人各有各的失败和卑劣,若想让自己心中美好的一面成长壮大,远离那些有毒的、计较得失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不把个体的坏嫁接成群体的坏,不因某些男性的恶行而对整个群体感到失望。人是多面体,好坏取决于你与他们的关系,靠近那些能让你更加美好的关系,远离那些糟糕的关系,这是上野千鹤子不对男性失望的秘诀。
#04
性和爱是可以分离的吗?二者是相同的吗?

答:“性爱”虽然是一个词,但“性”和“爱”并不相同。上野千鹤子说,将不同的东西区别对待,总比不区别对待要好。长久以来,针对女性,性和爱一直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球的性革命,才逐渐扭转了人们的这种意识。
认识性与爱的区别,就要从理解上世纪这场性革命开始。这场性革命想要颠覆的是近代的性规范,那时普遍的观点是:“女性忘不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女人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性成为了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而献给男人的东西。那个时候,没人关心女性的性需求,人们认为女人在性方面就是被动的。
到了后现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是有性需求的,女性也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快感和欲望了。萨特和波伏娃这样开放式的关系也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男女的理想。这些革命性的性实践颠覆了固有的性范式(只针对女性的“性和爱必须保持一致”的观点),揭示了“即使对女性,性和爱也是两回事,应该被区别对待”。
#05
恋爱是生活的必需品吗?我们为何需要恋爱?

答:“好想恋爱啊,好想脱单啊。”生活中,常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甚至有人为了求姻缘而去烧香拜佛。然而,从性别的角度而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那种“恋爱”其实很牵强。铃木凉美认为,对于异性恋而言,女性通过少女漫画、言情小说、偶像剧这种浪漫的爱的媒介学习恋爱;而男性,却通过成人电影学习性和恋爱。这样的两方要在不同的语境下分享同一个空间,想方设法将对方拖入自己的语境,未免强人所难。在许多恋爱关系中,一方渴望浪漫的爱,一方渴望拥有并满足欲求,双方偶然地相遇并因为“生育”这一社会任务而勉强实现了共存。
如果恋爱是这样强人所难的结合,为什么人们总是渴望恋爱,我们是否需要恋爱呢?上野千鹤子说,她始终相信,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的,这种经历是有总比没有好的。她说,恋爱是斗争的平台,你要夺取对方的自我,并放弃自己的自我。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互相伤害,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越的自我界限。
在恋爱关系中,人能够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恋爱会帮助我们懂得自己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利己心、宽容和超脱。恋爱是一种“面对对方时极度清醒,以至于在旁人看来无比疯狂”的状态。跟一个爱上“渣男”的女人列举对方的多少缺点都是徒劳无功,因为她一清二楚。
恋爱是必需品吗?就算没有恋爱,人也能活下去,也能认识自己,甚至也可以组建家庭。但能使你充盈、教你认识自己的,是“爱”而非“被爱”,是“欲想”而非“被欲想”。没有性和爱,人也可以生活,活得很好,但恋爱的确是“有”比“没有”更能丰富人生的经历。
#06
即使社会观念不断进步,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为什么许多女性还是如此渴望婚姻呢?

答:铃木凉美提到了奔四女性的生活实况,她们的恋爱烦恼几乎都归结到婚姻二字上。即便如今,女性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为什么她们仍然如此渴望婚姻呢?
人们总用“定下来”或“解决人生大事”来描述婚姻,不仅是因为结婚能让当事双方顺利嵌入社会固定和既有的框架里,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婚姻能够给人一个稳定的家庭,这个家庭象征着安全感和后盾。但是,就我们的实际经验和社会上的见闻来看,婚姻所给予的安全感大多都是暂时的,家庭很难成为一个永恒的避风港。
在社会观念下,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习俗,结了婚的人不需要回答“为什么结婚”,唯有不结婚的人会被反复问及“为什么不结婚”。如果我们问问结了婚的人,为什么结婚呢?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出于对家庭的渴望。家庭是接住你的底,是终极的安防用品。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认定,除了组建家庭,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没有其他的结婚动机。由性二元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家庭,亲子之间因为血缘而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夫妇之间也因为共同孕育了孩子形成了一个名为“家庭”的纽带。没有什么关系会比这样的家庭更显得命中注定、无法选择。上野千鹤子说,家庭二字之所以如此具有魔力,只可能是因为人们渴望这种无法选择的命中注定。
奔四的铃木凉美在书中提到,当看到闺蜜逐渐开始组建家庭,远离自己,开启了新的生活,而自己也送走了母亲,父亲也有意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她深深地感到自己无家可归,由此对婚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憧憬。
上野千鹤子对此的回应是,对于婚姻的渴望是阶段性的。看着朋友远离,亲人离世,人难免感到孤独,但独处是人这一生需要面对和修习的处境。即使有了婚姻,孩子也会离开、去拥抱新的人生,爱人也会离世,到头来,人难免孤身一人,婚姻和家庭并非是解决孤独一劳永逸的方法。
虽然随着社会观念的解放,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能够在家庭之外(比如工作)得到更多认可和成就感,但对于家庭(或者说寄托)的渴望是难以被其它方面的成就感抵消的,这可能也是仍然会有许多女性感叹“好想要结婚”的原因。
#07
为什么很多女性惧怕自称女性主义者?

答:铃木凉美观察到,如今活跃在社交媒体,积极为各种运动发声的是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对比铃木凉美的青春时代,如今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惧怕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氛围,女性主义热潮逐渐让日本的女性认为自称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曾几何时,许多人在网络上为性别话题发声、谴责性别歧视、抗议不公平的待遇时,总是会先申明“我不是女权,但……”。她们为什么会如此抗拒“女权”这一身份标签呢?
首先,有个很大的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是她们所排斥的女权是狭义的激进女性主义。很多女性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严厉地批判父权制,因为她们在学习和就业等方面似乎没有遭受到显著的性别歧视,在社交媒体上以“受害者”的姿态发声似乎也不合时宜。她们觉得自己并不属于“女权主义者”的群体,虽然曾经受益于女性主义(前人的积极发声带动社会进步),但现在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群体身份了。
除此之外,被严重污名化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女性抗拒这个标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上野千鹤子提到,“我不是女权,但是…… (I’m not a feminist, but…)”这样的话语是有前史的,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许多女性都说过“I’m not a lib, but…(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但……)”。这种句式的言外之意是,我对她们的观点有共鸣,但不希望被视为与她们一样的人。
在如今中国的社会语境下,许多女性不愿自称“女性主义者”,原因也是一些人将“女权主义者”一律称成“女拳”,将网络上女性的发声称为“重拳出击”,将“女性主义者”污名化为“不被男人爱的剩女”。污名化阻碍了国内女性主义者们勇敢发声、寻求身份认同、找到共同体的进程。
上野千鹤子谈到,90年代初的女性也是如此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女性运动产生的前提是“我们女性”这一集体身份认知的确立。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让人们在想象的层面上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因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感受,形成身份认同,达成共同体。
自古以来,对女性“分而治之”是厌女症最常用的手段,他们将“女性”分成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拎得清的和拎不清的,理智的和疯癫的。这也导致那些“懂事的”、“拎得清的”、“理智的”女性与被严重污名化的女性主义者们划清界限,掉入了陷阱中。如今,社会舆论总算逐渐将“我是女性主义者,我为女性主义发声”变成了“很酷的事情”。
“我们女性”这一身份登场,不论拎得清还是拎不清,懂事还是不懂事,我们都是女性。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这本书能够拯救女性”
父亲这本书
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位女性作家的20篇女性故事
深读这本书,让孩子敢于直面困难、拥抱美好
女性“自我解放”如何用文学达成
这7本书,带我们上一堂 积极的“生命课”
“拯救苍生是你的命运,但拯救你,是我的使命”
这才是成熟的新时代女性啊
FGA CHAT | 周宏翔:专注写女性群像的男作家
女性诗人刻板印象的再造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7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79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7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9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34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