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小说,是一块石头,包括阴影
原标题:他的小说,是一块石头,包括阴影

左起:李黎,谈波,韩东,曹寇,张德强
64年的谈波,朋友们叫他老谈。
老谈上周得奖了,因为小说集 《捉住那只发情的猫》 (简称《捉猫》),2022年度刀锋图书奖给出了这样的颁奖词:
书中的主人公们,与生活、宿命“死磕”——有时候是石头磕石头,有时候则是鸡蛋不得不磕石头,后者是谈波更想呈现的。书中收入的12篇中短篇小说,被比喻为12根火柴,有的温柔、温暖,有的灼热、猛烈,都有着让人一头扑进去的能量。而谈波的文字,类似于刀劈斧凿的木刻画,线条狠而简洁,由此产生力度感、速度感。
刚好不久前,老谈南行,和老朋友们聊了聊天,说起这部作品和彼此的交往。
韩东还记得和老谈第一次网友会面的震惊,“我的天哪,怎么是个老头”;曹寇说老谈是小说界的八级技工;年轻的朋友郑在欢,看完老谈的书后,连发了两条朋友圈......
我们节选了老谈南行的十个片段,借着这次机会,重新认识一下老谈。
嘉 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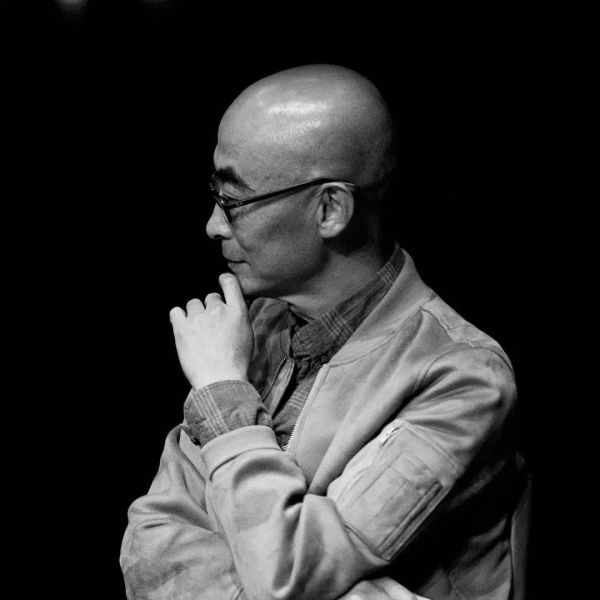
谈波
1964年生,居大连,八十年代起业余写作。小说多见于《今天》《人民文学》《野草》《青春》《鸭绿江》等杂志。已出版小说集《一定要给你个惊喜》《捉住那只发情的猫》。

韩东
主要写诗和小说。著有诗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及思想随笔集四十多本。获多种多项文学及其他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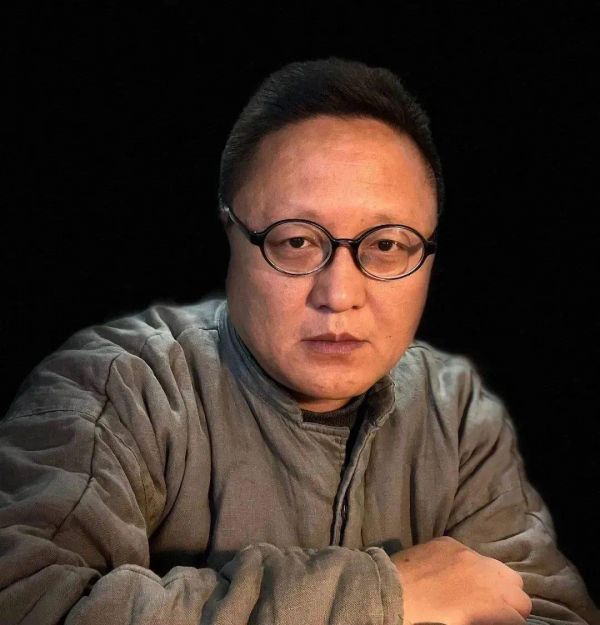
曹寇
南京人。出版有小说集多部,长篇一部,另有随笔和其他作品若干。

魏思孝
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

郑在欢
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长居北京。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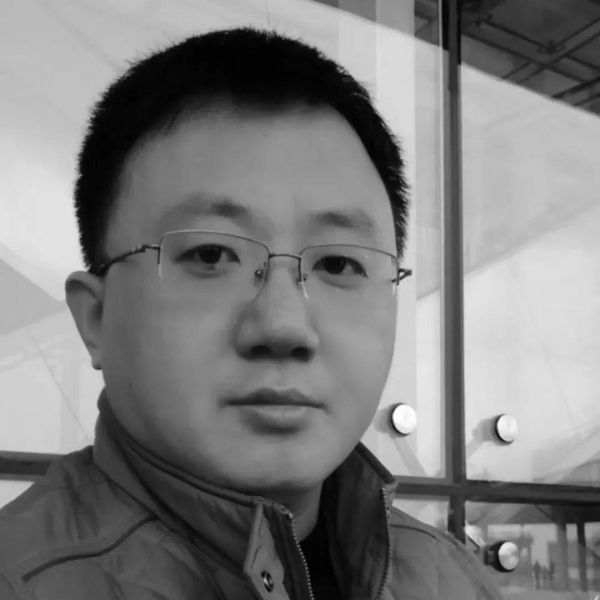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1999年开始写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诗集《深夜截图》《雪人》。

赵步阳
文学评论家,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黄建树
生于湖北宜都,现居湖北武汉。上班时编书,下班后读书、买书、译书,以及养娃。译有《成为母亲》《超凡脱俗的鸟》《早春》等。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01
韩东:我的天哪,怎么是个老头
李黎:这本小说集出来之后,我收到一些反馈,有人看完会非常惊诧,说写得怎么这么好,也有人说写的什么东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小说集都让人感到吃惊。还有很多人认为作者应该是个90后,怎么也想不到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大爷,他文字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纯粹、那种感觉,是让人很奇怪的。结合这两个惊讶,请老韩跟大家聊一下,你怎么定义老谈的写作?
韩东:我一贯地认为,不管老谈这个书出没出来,他都是中国写短篇小说写得最好的作家。这话挺得罪人的,因为曹寇、在欢、李黎他们都是写小说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么一说,也说出了他们的一种观感,并没有因此觉得不服气。只要你是写小说的,认真写作的,对老谈所达到的高度,我觉得大家肯定是有一个共识的。
和老谈我是第二次见面,以前有一些文学论坛,我就在网上看他的小说,他那会儿的网名叫“看见了”,反正每次必读,一直觉得特别好。但是对这个人确实不太了解,包括年龄、性别,想象当中应该比我小很多,至少是70后。一直到六年前,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说老谈我们见一面,那个时候还叫他谈波,因为不知道年纪。见面一看,我的天哪,怎么是个老头,他是64年的,就比我小三岁。但是一想那样的小说,不仅是技术层面,包括他写的那些事情、人物,也只可能是这个年龄层的人才能写出来。
老谈不仅写作有他的标准,他怎么去从事写作这件事儿也有他的标准,做人也有他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老谈绝对是一个异类,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写得好,在某些方面真的是一个写小说的标杆,他完全不会经营,不会混,就坐在这儿。
李黎:老谈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投入的人,抽烟喝酒不烫头,游泳打麻将,反正一个退休老干部所有的喜好他都有,而且好像因为打麻将,一度把颈椎都打得出了点问题,就是特别热爱生活。同时他在写作这个事情上又特别纯粹,只顾闷头写,然后一直写到极致。
02
老谈:《捉猫》这篇最感谢韩东
谈波:九十年代,我看到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后,就到处找他的诗,还给抄下来,现在还在家里保存着。就像塞林格说过,他如果看到一本好书,他会想给作者打一个电话。但是我不好意思给我敬仰的人打一个电话,所以始终记在心里。
后边有了论坛,我就在“橡皮论坛”看到了韩东,感觉找到了自己一个精神家园,特别开心。那会儿每次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论坛看别人的帖子,就感觉到好像一个特别压抑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释放一下自己了,自己也贴一贴作品看看有没有人回帖,在上面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存了韩东的电话,也没好意思给他打,哪怕问候一声,当时还有聊天室我也都没好意思进去。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说,我说献给谁,列了三个男人的名字,当时张浩民还讽刺我说,你应该献给哪个姑娘,你献给我们干什么?然后六七年前,一个电话响了,韩东的,就回到《捉猫》的故事了。
《捉猫》这篇小说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韩东,因为最早我是准备把它当作一个小长篇去构思的,在这之前我写的都是一些很短小精悍的艺术小说,而且我也确实坐不住。我思考的方向也是偏向于那种精简的、极简的,我把起承转合就选了两个点,有时候选了个起,选了个转,小说就结束了,没有那种完整的东西。
然后我就把这种困惑跟韩东倾诉了。他有一种特别的美德,就是他很愿意无私地、一股脑地把热情喷发出来,让你去完成他认为你应该完成的一些事情。他在电话里,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鼓励我: 老谈,你没有问题。我一听就热血上头了。在我非常尊重的人和非常喜欢的人面前,我不能也不愿意掉链子,我就决定要把它写完。我用了10个月写完了,当时给它打了个70分吧,直到把它收进这本书里。
滑动查看活动现场
嘉宾:谈波、韩东、曹寇、李黎、郑在欢、魏思孝、张德强、赵步阳
03
曹寇:老谈是八级工
李黎:我最早听说老谈是曹寇讲的,曹寇不断跟我们谈老谈,他只有两个词,一个是高手,一个是高人。请曹寇聊一聊,你为什么认定他是高手?
曹寇:我跟老谈都是在文学论坛玩的,在“他们文学论坛”之前,我们就在“新小说论坛”、“橡皮论坛”认识了。我当年刚开始写小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东西贴上去,希望得到反馈,唯一给我积极反馈的,或者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反馈,就是谈波。谈波对我有知遇之恩,真的,对我有点拨,有启发,他是我的人生导师之一,他是最早肯定我的写作的一个人。 所以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对待。
后来大概在十年前,我去大连做过一次活动,那是我跟谈波第一次见,当时他讲话我基本听不懂,满口大连话。但是谈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很朴实,一点没有文学青年的架势,更没有作家的架势,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市民,他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像很多人,一辈子热爱文学,家庭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工作也是颠三倒四,很多人热爱一个东西,就会把它作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窘迫、无能、颓唐、一塌糊涂的借口,被文学害了。
但老谈不是,文学没有害了他,恰恰是文学滋养了他,把他养得头颅雪亮,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老谈很热爱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他身上不仅看不出痕迹,还使他整个人的状态显得极其丰盈。
对于文学写作这个行当,我们往往会用才华、天才这些词,其实写作这个东西是可以教的、可以学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成名的作家,大多数人的写作还是处于一种学徒阶段, 但是老谈的写作属于八级工,就是最顶尖的那一拨。当然我这么说,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就吹嘘朋友,吹不吹嘘,完全是一种自我判断,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判断也很容易被其他东西裹挟,比如获了一个什么奖之类的。我的标准就是觉得他是八级工,因为我觉得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个人的。
04
魏思孝:他是中国文坛的硬骨头
魏思孝:我看谈波老师的小说,不太敢多看,因为每次看的时候就让我特别有想模仿的冲动,但是这些东西又写不出来,让我特别焦虑。 他是中国文坛的硬骨头,这个形容和他小说呈现出来的气质也非常契合,就是剔除了一些没用的语言,留下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曹寇:老谈的小说基本上全是干货,没有水的、多余的东西。我想起老谈二十年前的推荐,从大连给我寄了一本书,是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巴别尔的小说,跟老谈的小说在质地上有相似之处,非常干硬,也非常震撼,就是一块大石头那种感觉,没有多余的花草、水分、昆虫,就是一块石头,以及它的阴影部分。 老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块石头,包括它的阴影部分。
《hello,树先生》
05
赵步阳:老谈的小说是马赛克一般字字雕琢
赵步阳:我想起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大连开会,会上发了好多书,我想把这些书寄回南京,就约了快递六点半来寄,结果等到大概快八点,快递小哥还没到。我就给那哥们打电话,结果那哥们接到电话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把我笑坏了。他说:老子不干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哥们特别大连,或者像大连人说的,特别彪。我那天晚上就一直在想,我想要认识这哥们儿。
不久后,老韩让我来写庆和、曹寇、小平和老谈的一个评论,后来这个评论发到了《今天》上面。我因此就系统读了老谈的小说,就是那本回声书店出的《大胆使用了绿色》,读了之后我非常震惊,而且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快递小哥,我觉得老谈写的这些人就是那个哥们的状态,特别彪,很无礼,但是又特别生动。
我记得是老韩说过的,大概意思是,老谈的小说是马赛克一般字字雕琢。我自己的观感也是这样的,他的小说篇幅是很短的,像那种马赛克的小瓷砖,但是一片片贴起来,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东北生活场景。
谈波:小说里以身边人当模特的成分肯定是有的,自己的经历肯定也有,然后也有看到的。 实际上小说无非也就是就像老生常谈说的,记忆力、想象力和观察力,都是从这三方面来的,一个是观察,一个是过去的生活,一个是想象,然后再混合一下,你再有所选择地调和一下它们之间的比例和浓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方式,但是大致的方式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6
郑在欢:读完连发两条朋友圈
郑在欢:我看到最后一篇同名小说的时候非常激动,一是写得太好了,二是写得太长了。 我们喜欢老谈的小说,是因为他的小说像小飞刀一样,一篇一篇非常短,两三千字就是一篇。这些小故事读起来特别快,但是里面韵味,或者说内涵,总会让你浮想联翩,尤其我们写小说的人愿意看,它会刺激你。谈波说他在电脑前很难坐够十分钟,突然之间,他有了一个那么长的故事,六七万字,让我们很惊讶。
谈波写的大多数故事是发生在他身边的,像这本小说里的《长春炮子》《大连彪子》。《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写了东北人在广州的故事,他写90年代末,一上来就是一个骗子,还有飞车党,这种很街头的东西,然后他把街头混混和和大学里的诗人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特别妙。直到故事的最后,突然出现一只发情的猫,它跑了,因为这只猫,后面故事连在一块,我是真的拍案叫绝。
《疯狂的石头》
如果你喜欢盖·里奇或者《疯狂的石头》,你看了这篇绝对会喜欢。当然谈波绝对不是模仿,《捉住那只发情的猫》是多线叙事,里面的人物很多,最后聚合在一块,形成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精彩的故事 。谋篇布局,就像工程师画工程纸一样,画到最后“啪”合在一起,那感觉,最后是智力的愉悦。当然是智力的愉悦还在其次,首先是这些人物的鲜活。 反正我当时读完,连发两条朋友圈。
07
张德强:我想起久违的家乡
李黎:这几年东北的几位作家可能风头比较劲,老谈出来之后,很容易就被纳入这个范畴。我觉得他和班宇、双雪涛其实不太一样,但是老谈又确实写过关于大连、长春的一些人和事。请德强,一个从东北走出来的,可能也不太想回东北的一个评论家、学者,来聊一聊东北的作家。
张德强:谈老师的确不是当下意义上的“东北作家”。人们通常理解的东北故事,往往和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下岗潮有关系,看上去有点惨;或者呢,就是春晚小品或抖音小视频中呈现的有些“可爱”的东北口音。谈老师的小说,比如《长春炮子》《大连彪子》,地名都显示了——这是在东北发生的故事,但又不局限于历史上的“下岗”或地方特色。事实上,东北面积绵延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个亿,东北故事的丰富要远过于三十多年前的所谓下岗潮,对东北历史的沉淀也远非几句感伤可以承载。
比如,《长春炮子》这个作品,所写的恰好是我上大学那年前后发生的事儿。我是1999年到长春上大学的,此前一年,长春一个黑帮老大死于火并,传说中他葬礼的花车铺满了整个斯大林大街。当时我接触到的,是一个官方的叙事,便是恶有恶报而已。而谈老师这个小说呢,好似旧事重提,把这故事再次讲了一遍,但用的是当事人的怀旧口气,在市井风气中掺入了几分侠义,细想想,怎么可能完全是“盗”而没有“侠”呢!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曾经是90年代混社会的旧日小兄弟,如今沦落为社会底层,他用一种非官方口吻——其实也不是一种完全可靠的信息源,夹杂着大量自己的美化在里面。整个小说全是第一人称讲,一直到最后一句话,他忘情的讲述全部用双引号标识。小说的间离感就来自这几乎遍布全篇的双引号,这代表作者并非全然认同讲述人的立场。但是,我们实在地看到一种民间视角,它跟官方的价值观存在着视差。这种叙述中的视差,又并非仅仅源自价值观差异,还有我们究竟是从哪个渠道进入“现实”的差异。不知道各位能否理解我这个东北人的感受,在黑老大葬礼的同时,在这一切模糊而峥嵘的画面中,电影《钢的琴》的故事,正在东北大地上发生着呢。我想起了电影《美国往事》,一个在滤镜中混乱而美丽的世界。
《钢的琴》
这本书的第一篇作品《大张的死与她无关》,我看最初几页时,还以为作者就是写一个东北老球迷没落的故事——这可太俗套了,我的邻居中就有很多这种整天怨天尤人的老球迷。结果,读到第四页,故事开始有了一种自然又超现实的寒气——本来无牵无挂的老张,突然冒出个疯媳妇!其实细想一下,并不算超现实,这个男的,老张,90年代初足球俱乐部制刚兴起时的球迷领袖,做啥事情都靠热情去奉献,不求回报,开心就好,就是东北大厂矿时代的一种风气和情怀。结果社会变得好快,一切都变了,规则也变了,俱乐部越来越商业化了——原来足球俱乐部的兴起是时代的挽歌而非进步的号角。过去的规矩落伍了,大张就难免成了过时和落伍的象征,所有倒霉事都在那一刻摊在他头上,他哥也不管他了,大张在十冬腊月里住在一个寒冷的破仓库中苟延残喘,还是兴致勃勃地去球场助威呐喊,是不是很像一个当代的孔乙己?
有一次看球时,因为一个没预料到的事故,大张从看台摔下,摔了个头抢地,没人在意他。他挣扎着起来,咳着血,以为自己没事儿。回到破仓库,他其实已经神志不清,大概是脑出血。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的女人说——老公我带你去看病去,她真的找来个板车拖着大张去医院。小说写到这里,我们大致理解为有点超现实的意味了,但又那么真切自然,不知道哪儿来的女人啊,板车啊,大张沉重的身体啊,说实话,谈老师写到这里,很有点卡夫卡的味道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女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男人,大张,已经死了,他的身体又那么沉重,她实在拖不动了。她索性把车上的人一丢,回自己家去了。她敲了敲自己的家门,和母亲解释一下自己为何离家这么久,然后这女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
这个故事的讽刺意味在于,这个相亲多年屡屡受挫,精神都不咋正常的女人,经过和大张的一番遭遇,经过大张的死,最重要的是,经过了自己对大张垂死的束手无策,她竟然被“治愈”了……被“治愈”的她,仿佛彻底忘了世上有过大张这么个人了,开始“正常”的生活。
我今年四十多岁了,我的父母一辈亲身经历过很多历史剧变。大张代表了那种东北人才懂的工业时代的浪漫,某种意义上他有点末路英雄的意思。但英雄要是倒下、没落的话,是没法被承担的,你没法背得起一个身体失能的英雄。在英雄没落之后,在几十年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命名他、回忆他,怎么记住他,所以你只好忘掉他,就像那个不知哪里来的女人忘记大张。这是小说中暗含的深沉隐喻。
谈老师虽然写了很多看上去残酷的故事,他内心却是非常宽容、温柔的,他让我想起久违的家乡。刚才李黎说的也许没错,我不一定会回家乡定居了,我记忆中的家乡已经改变了太多。但我的家乡,借助谈老师这样的写作者,会永远被记录保留下来,不仅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历史的印痕里。
08
《零下十度蟹子湾》:市井凡人的尊严
郑在欢:我第一时间读了试读本,试读本第一篇是《零下十度蟹子湾》,这篇小说的男主角是个捕蟹子的,脾气特别倔,然后谈恋爱了。男的说我之前有过什么,沦落到这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我这个人“受不了屈儿”——这个故事的关键。就是说这个男的不能受欺凌,只要是我愿意干的,再苦再累的活儿我都可以干,但我不能让人欺凌我,就是我的尊严不能被压制。
主角后来出了一个意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女的和小工就想帮他讨回工资。这个小工叫锅底子,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底层的人,就很能受屈儿,只要给我口吃的,我都能吃得下去。剩下这两个人都算弱者,锅底子一直都没有真正像个男人那样,故事是以女的向老板复仇结束。
今天活动起的名字是“市井凡人的尊严与信念”,我觉得特别好,市井凡人的信念很大一个程度就是尊严。这本书里面基本上在写人的尊严,在写人怎么在乎自己的尊严,人的尊严怎么因为生活或别的被人践踏。大多数时候,人成年了可能没有这种感受,要收起锋芒。 但是谈波大部分小说是在想着怎么才能让市井凡人获取尊严。
黄建树: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有点想到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小说中那位女性角色,她其实就是有一种侠义精神,为她的爱人复仇。
郑在欢:她为什么会复仇?她也不是为了尊严,她也受惯了凌辱,当惯了弱者。但是她在乎她爱的人,这个小说动人的地方是她是为她爱的人,维护他的信念—— 尊严。我再读到后面的东西,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乎的尊严,都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江湖儿女》
09
《长春炮子》:一个妙的结尾
郑在欢:谈波的一个“亲读者”告诉我《长春炮子》是谈波看快手写出来的,他给“偷”过来,写成小说了,他写街道上的传奇小礼哥,他怎么服众,还有别的人物,写得特别传神。这个就很强,一个是他的小说,一个是他身边街道上的人,另一个是快手,是更广大的民间。
黄建树:我当时看这小说的时候也很好奇,甚至去百度上找长春90年代黑社会老大有谁,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没找着。另外,我是想讲一下《长春炮子》让我想到《大人物盖茨比》(现通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一上来有一个“我”,在回忆。《长春炮子》里面也有类似“我”这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保安,这个保安发现“我”在抖音上听别人讲礼哥的视频,顿生亲切,然后通过保安的叙述引出了礼哥波澜壮阔的一生,有一些传奇性在里面。
谈波:对,《大人物盖茨比》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叙述,通过叙述者的表述,好像非常真实。《大人物盖茨比》特别丰富,不单有一个盖茨比的故事,它还有一个“我”成长的故事,还有他对盖茨比的评价。我这个就比较简单,有一个叙述技巧,作者、叙述者、叙述对象,有一个序列的轻重,这个关系如果协调好了,在任何一段空间当中可以去给它放大缩小。 当然这些技巧我认为不是很重要,只要你是用感情,用直觉去把握,在叙述过程当中就自然而然抓取到了。
黄建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长春炮子》的结尾,很妙。
郑在欢:我就想说那个。 谈波刚刚说技巧不重要,那可不是,短篇小说看的就是你以一种什么方式讲故事,而且结尾如果收得好了,那个点上来,就都妙了,它能打到人。这是技巧的东西,当然首先是对人物真的有情感。
小说前面先说礼哥仁义、仗义,但毕竟是在道上混,最后因为一场婚礼,两伙人打起来了,然后莫名其妙,礼哥就在混乱中被捅死了。讲故事的人讲到这时候,突然就收了。小说最后一句话特别酷,是一个动词。
“战场归于沉寂。
“搪瓷脸盆在崩瓷,劈劈啪啪,一声紧过一声。
“二道的炮子们,四面八方往这里急赶。”
到这就结束了,你意犹未尽,你还停留在小礼的死的混乱之中,茫然之中。一下子在动作中停下来,留给你一个很震撼的场景。他们要干架了,可想而知。
《钢的琴》
10
作品主义与作家主义
李黎:老韩写小说有一个极端的方法,他写完第一稿之后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在电脑里面把原来的文档删除,然后拿着稿纸重新录入一遍,非常苦行僧,甚至有点变态。按他的说法是确保小说没有漏洞。老谈,你的小说是一气呵成,还是改过很多遍?一个作品大概能磨多久?
谈波:实实在在讲,我是没有定力、坐不住的那种人,所以我一般也驾驭不了篇幅过长的小说,但是偶尔也写得比较顺畅,写完有一种顶峰体验特别开心的那种感受。我最近也有点想把篇幅逐渐拉长,《捉猫》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再说也有一些你自己想表达的,是短篇无法呈现的。
前两天我刷到了刘按的公众号,他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他用了15天时间写完了一个长篇,而且马上就可以拿到去出版,我看完就震惊了。我就想我能不能也用一种长篇快写的方式,不用这种零打细敲的雕琢,我现在只不过是在这儿想,到底能不能做到也是个未知。
韩东:老谈我觉得你不用写那么快,也不用写那么多。老谈的小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密度很大,他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要把很多东西灌进这样一个空间里。 我认为老谈其实是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或者当成诗歌来做的,做一件是一件,是那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作家可以粗粗地分为两类,一类可能就是叫 作品主义,就是个人跟作品的距离越大越好,我可以消失,但对作品质量的要求就会非常的高,不在于多;还有一类作家,可能叫 作家主义,我写的所有东西加在一起,等于我,所以他就不断地写。除了写作方式的习惯之外,可能对文学的期许也是不一样的。老谈这样有薄薄的一册子,一星期就能看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其实也是我的理想。
谈波:这个肯定不仅仅是我,所有在座的写作者,甚至想写作的人,之所以要写,肯定是想写一个能传世的东西,想写一个最好的东西,那样才值得你去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个是必须得诚实的。
一个彩蛋
左:谈波;右:韩东
延伸阅读
大哥你写小说,你写他有啥用啊?
活着,就是和一切“巨大的看不惯”死磕
最柔软的人,最坚硬的故事
《捉住那只发情的猫》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他的小说,是一块石头,包括阴影
男人每天都刨一块石头回家,连续几十年,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
如何让一块石头看起来十分柔软?
他鱼塘挖到天价石头,专家:底下还有切记保密,他一守就是10年
夜雨丨谷与麦:鸡蛋、石头和一条悖论
画说民俗 | 正月初十 石头节
通讯:在石头上作画的“80后”斜杠青年:每块石头都是“可塑之材”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是什么歌 雨花石歌词
3种“石头”捡回来养花,“丢1点”到花盆里,土壤松软,根系壮
挥挥手,让阴影消散殆尽;点点头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62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6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22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