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魏微:《烟霞里》写故乡,也写都市人身上的“游离”
原标题:作家魏微:《烟霞里》写故乡,也写都市人身上的“游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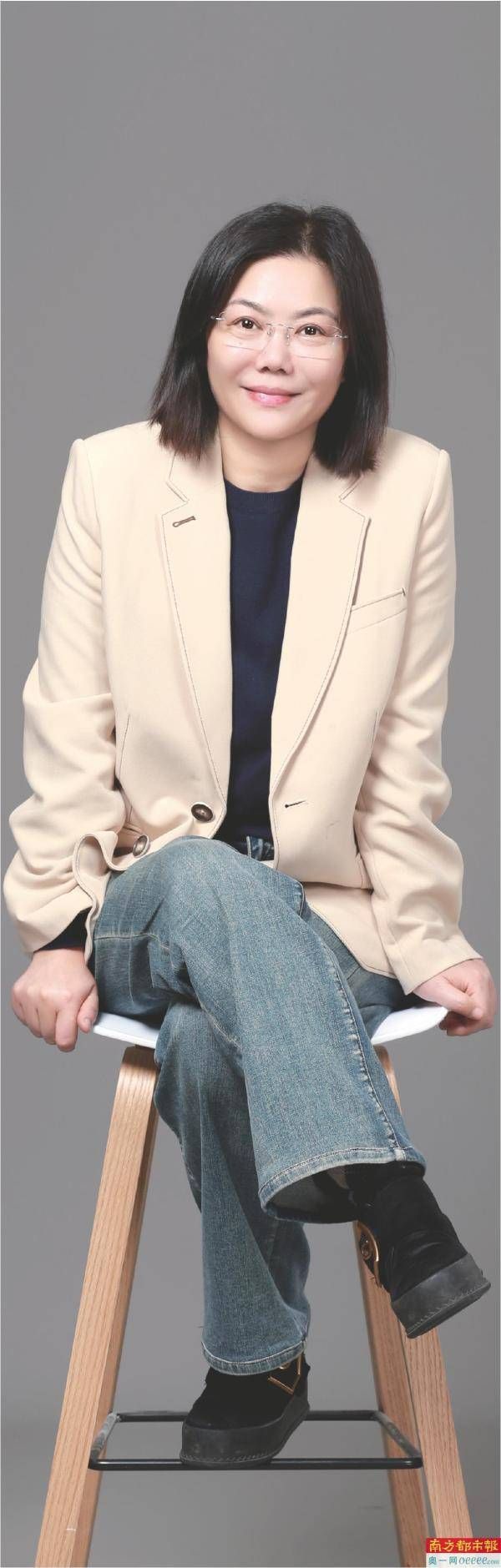
受访者供图
魏微小说家。作品曾登1998、2001、2003、2004、2006、2010、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代表作品为《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一个人的微湖闸》《烟霞里》,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在作家魏微眼里,烟霞既有美丽绚烂的一面,也有虚无飘渺的一面。魏微说:“《烟霞里》写的是人生,我自己的理解是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
2023年岁末的一天,作家魏微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为读者朋友们带来线上讲座“一代人,烟霞里”,分享她的创作经验与人生感悟。
魏微,江苏人,1994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现居广州。长篇小说《烟霞里》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魏微的转型之作和心力之作。2023年新春,在《烟霞里》刚出版之际,魏微就接受了南都记者朱蓉婷的专访(详见2023年2月12日南方都市报A10版《魏微:写作必须真诚,字里行间见生命》)。当时她表示,“2005年移居广州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而在南都读者俱乐部的线上分享中,魏微进一步畅谈了她写作《烟霞里》与广州的渊源等感悟。
《烟霞里》以时间为经线,以女主人公田庄的经历为纬线,用编年体的方式,逐年检视和回顾了一个女人繁茂又寂静的匆匆一生。田庄出生于1970年代内地的一个小山村,然后读书、上班、结婚、生子,直至英年早逝于广州。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的一生,亦与整个国家在这四十多年中的发展变迁同步。
在线上分享会中,魏微围绕小说《烟霞里》的编年体结构、叙述视角和叙事策略,小说中展现出的故乡、女性、乌托邦等议题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她强调,小说虽然十分新颖地采用编年体形式,但并未严格按照编年体来写,而是采取上下挪腾的方式,扩大了叙事空间,书写了近百年的几代人的人生历程。由于重点在于塑造人物而非讲故事,小说最大的看点是“在日常生活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发现的趣味”。
有评论家曾经指出,魏微写《烟霞里》意在为70后一代人立传。在分享会上,魏微坦言此种说法并不确切。她说:“田庄的70后一代的理想主义的特征,在小说里其实没有得到展现,所以我的重心并不在于写70后。我可能在无意间概括了一个比70后更大的群体,这群人生长于乡村和小城,落脚于大都市,在这几个地方游离,故而我写故乡感、写异乡感、写都市人身上的游离。”
线上讲座部分实录
关于书中的“烟霞”与“创世”
主持人:《烟霞里》扉页的“献词”引了唐人王质的诗句“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请魏微老师谈谈在“烟霞”一词上寄予了什么样的隐喻,或者试图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意境呢?这“烟霞里”是李庄、是清浦、是江城、是广州,还是中国,抑或是一个时代?
魏微:“烟霞”是古诗里一个常用的意象,唐诗、宋诗里面都有。我觉得作为意象,其实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这篇小说主要是写人生,我自己理解就是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回望的时候,可能会看到“烟霞”,有美的一面,有时候又虚无缥缈,我是从这个意象上来理解的。小说里头有一些关于“霞光”的描写,还不单是在2010年。我印象中写1980年的时候,田庄的妈妈孙月华带她回乡下的外婆家,骑着自行车,看到霞光、晚霞照在田野上,那种秋天的丰收场景,这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始来临。这种意象挺多的,包括1977年,我印象中1977年恢复高考,田庄的爸爸田家明知道了这个消息,似乎也有一些关于霞光的描写,这段我不清楚后来是否删了。包括1970年代末期写到他们家搬到县城,孙月华从一个农村人来到县城生活,萌生出一种进城的欢畅感,那时候也写到了霞光。
主持人:《烟霞里》书中多次提及“创世”,第一次是小丫一岁那年的春节,孙月华生出他们一家将开天辟地的“创世”豪情;第二次是田庄爷爷,当年的田伢子从军那日的诞生感与对于田氏家族的“创世”意义;田家明年少演唱《国际歌》的场景也隐含着一种“创世”的感动。请问“创世”在你的叙述中象征着什么?
魏微:《烟霞里》里有两处写到了“创世”。第一处,是田庄刚满月的时候,过年正在放鞭炮,她妈妈抱着她,生出了一种创世的豪情。第二处就是她爷爷离开了乡村去参加革命,我在这里写到爷爷才是真正的创世者,他把这个家族从乡村带到了城市。我当时写到“创世”这个词的时候,尤其是田庄满月的那一天,孙月华生出的那种创世豪情,其实我是联想到了“创世纪”。与“创世”相关的一个词在小说里也有写到,就是“造物”。田庄刚生下来的时候,爸爸田家明非常感动,小说里就写到这个爸爸想到了“造物”这个词。
“创世”或者“造物”对于个人、时代或国家民族其实没有什么隐喻,如果要有隐喻,就是对于人生的隐喻,即一个生命的诞生。对于父母而言,尤其是对于初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头生子这种生命的诞生于他们而言非常新鲜喜悦,可以说是类似于一种创造的、创世的感觉,小说里也提到了新生儿的诞生都如同神迹。这其实是我对于生命的理解,身为父母的微妙的荣光的感受。
当代小说中首次采用编年体结构
主持人:《烟霞里》在极富创造性地采用了编年体的结构方式外在之下,魏微老师还赋予了这本书以更丰富的内里。在田庄一岁到四十岁的编年记忆中,不断采用倒叙、插叙或预叙的方式,层层叠叠地叙述田庄的人生经历。想请魏微老师谈一谈,你是有意地在编年体结构下加入主角与群像的纪传叙事吗?
魏微:对,我很高兴编年体结构第一次运用在小说创作上。严格的编年体,就像陈寅恪编年、梁启超编年,这种一年一年的、从出生一直记到辞世的结构形式,在当代小说里应该第一次应用。我也很高兴自己采用了这样一个新鲜的形式,但这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小说如果严格地按照历史人物编年体来写,很容易把小说写死。我觉得小说需要更自由一点,倒叙、插叙、未来叙事,才能挪腾出空间来。可能也是跟我这些年长期读年谱有关,我会考虑到小说叙述的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形式上是编年体,但实际创作并没有严格地按照编年体来,而是采取了上下挪腾的方式,扩大了叙事空间。因此这部小说看上去是写一个女人的人生40年,其实她的挪腾空间并不止于此,包括她的爷爷辈,等于是二十世纪都写到了。爷爷是生于1913、1914年左右,他做放牛娃时是30年代。所以,《烟霞里》貌似是写了人生40年,其实也算是写了近百年的几代人的人生历程,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田庄身上,以田庄为中心带出了一些主要人物,比如爷爷、爸爸妈妈,以及田庄来到广州后的友情、爱情,一个女人的一生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主持人:编年体结构不可避免要面对叙事被均等分配的问题,这对于小说的戏剧性似乎有碍。然而《烟霞里》的叙事性依然很强,故事丰满可读,请问是做了哪些努力来点石成金,把这种时间均等的结构变为叙述优势?
魏微: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或者说可读性还是有的,但可读性不在它的故事有多么好看,而在于它的人物。我在写作时把精力都用在写人上了。我觉得对于文学而言,可能最重要的是写人,而不是写故事。所以《烟霞里》虽然没有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但因为我写出了人,包括人的个性、人和人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其可读性就在于此。主要在于我写了人与人际关系,可能跟大部分人的人生经验是共通的,就会有读者缘。那如何写人、写人际关系、写生活,我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写。比如田庄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那就通过写她身边的人际关系,写她的爷爷、爸爸妈妈,写奶奶和她妈妈的婆媳关系、围绕在田庄身上的七姑八姨的关系。这其实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这种熟悉会吸引读者读下去。有一个朋友曾说,我擅长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描写,在吃喝拉撒、锅碗瓢盆这些特别不容易出彩的地方能够写得引人入胜。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特长,我对于日常生活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总能发现趣味。比如小丫,田庄小时候叫小丫,小丫六岁的时候她叔叔带了女朋友回来,小丫这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吃醋了;还有小丫周旋于她妈妈和奶奶之间,这对婆媳关系不太好,而小丫又很灵光,就周旋于她们之间;还有小丫爸爸妈妈打架,他们姐弟两人在拉架。这些都挺有意思,我创作的时候都忍俊不禁,我写进去了就觉得很好玩。
主持人:魏微老师在前序里提到《烟霞里》的叙述人“均是她(女主田庄)的生前好友”,用朋友的视角来叙述田庄的人生故事,用友情去叙述亲情。在这独特的叙述视角里,请问作家本人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朋友、是书中所说的小说家魏微,还是镜像的自我呢?
魏微:小说里有小说家魏微这样一个角色,写作的一开始并没想到这样,给她的笔墨比较少,这是比较遗憾一件事,其实可以多给小说家魏微一些场景和戏,但因为太赶时间就顾不上了。小说家魏微在《烟霞里》是田庄的一个朋友,这篇小说后来的叙事主体变成了“我们”,小说家魏微是“我们”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几个人共同做一件事情,为网友写回忆录,构成了这篇小说。
主持人:《烟霞里》一开始就提到“她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1990年代的所有的年轻人”,魏微老师笔下的田庄,一个将老未老的女青年,田庄的记忆是你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想问你觉得田庄所象征的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
魏微:很多人都在问,田庄是不是有我的影子,是不是自叙传?有一点,但不全是。她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有一点点影子,到了大学、来到广州,田庄的经历可能是我身边很多同龄朋友的生活经历糅合而成,所以我觉得田庄是个70后。就有评论家问我是否在为整个70后一代立传?我不承认,我觉得自己没有,也没有意向要为一代人立传。一方面我没有意愿去为一代人去立传,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做到。但我承认田庄的经历可能是超越了整个“70”一代人。超越了一代人的是她是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大都市的一群人的共同经历。如果要说我是要为什么人写传记的话,我宁愿说是为田庄写。
我的责编樊晓哲老师说田庄身上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现在的年轻人也会有。所以田庄虽是70后,但这部小说,我的重心并不在写“70”一代人。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70”一代人可能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田庄“70”后一代的理想主义的特征,在小说里其实没有得到展现,所以我的重心并不在于写70后。我可能在无意间概括了一个比70后更大的群体,这群人生长于乡村和小城,落脚于大都市,在这几个地方游离,故而我写故乡感、写异乡感、写都市人身上的游离。
主题不是故乡,但我对故乡有话说
主持人:田庄的一生似乎有很多故乡,她抵达,身处,游离,徘徊,回到,却又观望。在她的许多故乡之间,她似乎都有归属,却又好像没有归属。而其余的人也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乡,如母亲要离开的故乡是李庄,要扎根的故乡是清浦。除了这些具象的故乡,田庄还有自己抽象意义上的故乡,“童年,人生的故乡”,而她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这个故乡。你觉得,故乡究竟在哪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我们应当如何处置和故乡的位置、与故乡的联系?
魏微:故乡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词汇,我觉得还不单在当代小说,其实在古诗词里故乡就得到了太多的描述。所以小说里有一句话,大意就是故乡被这个汉语词汇“故乡”压得太重了。当时小说将要完成准备起名字的时候,责编樊晓哲想起一个名字叫“山河故里”,后来我不同意,因为虽然我对故乡有话要说,但这部小说我其实还不是要写故乡。即《烟霞里》的主题并不是故乡,其实是在写人生。但这部小说里,对于故乡我总归还是有话要说。
“故乡”这个词,我直到今天也没想好。我曾经在一个访谈里说到,现在我们都市人,其实每个人都是异乡人,极少有人终身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往往都要离开,又回去,再离开,处于一种迁徙状态。但一说到故乡,大家都很怀念。我曾经说过很多人对故乡都抱着一种一厢情愿,就是中国人对故乡的情结。但在今天,我又觉得对“故乡”这个词汇,我们是不是太过于一厢情愿,或者说自作多情?很多人对于故乡有一种诗意的想象,觉得我将来还是要回去的,过一种乡居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乡村有一种莫名的诗意的宁静的想象。其实真回去了,乡村就还是那个乡村,而且真回得去吗?我记得鲁迅在《风波》里写到一群知识分子坐在游船上观赏河边的村庄,发感慨地说真是一幅地道的田家乐,然后鲁迅就把笔头一转,转入了这个乡村的内部,写七斤、九斤老太等各种鸡零狗碎的东西。我觉得挺讽刺的,其实这个才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故乡的这种怀想、想象,有时候可能是一厢情愿,现在中国人与故乡的关系挺矛盾的。“故乡”这个词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词汇,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词汇,但我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在这篇小说里,我稍微触及了这个概念、这个词汇,但也没有深入地探讨,因为我也还没有想清楚。我觉得当代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感情确实存在,但对于故乡的理解又太简单了,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出来,也是提醒自己对于故乡的态度。
主持人:《烟霞里》在历史的语境里建构了一个女性的世界。以女性孕育女性开篇,勾画了几代女性的生存与抗争、窘境与坚韧、命运与爱。这些女性都是不完美的,没有全然脱离男性而成就完备的女性自身。请问魏微老师,你是如何看待这一代代的女性和她们不同的窘境与抗争呢?
魏微:我觉得田庄还行,田庄还是自洽的。问题里“没有全然脱离男性而成就完备的女性自身”这点应该不适用于说明田庄,她在男女关系、和男性的关系上比较独立,比她妈妈要强。她妈妈孙月华虽然强悍,但身上反而没有独立性,还要依靠男人,田庄这方面倒还好。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但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贴着女性主义去写,生活或人物都是大于概念的,所以我会跳出女性主义的思维陷阱,还是贴着人物来写。一些女性读者可能会不满意,因为我的小说里对于女性会有一些反省、讽刺,让她们觉得受到了冒犯。前几天在广州做了一场分享活动,我们身边有一个同年龄的男性批评家反而觉得这篇小说对男性不友善,我觉得也都还好。我对男性当然有一些讽刺,但我对女性其实也一样,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写到某一步顺便带出来的,并没有刻意要去展现男性的弱点、女性的弱点,而是跟着小说走。
主持人:小说的叙事似乎难以脱离“乌托邦”的议题,在小说的中间章节《1990年 二十岁》中提到了“没有完美的社会,除非是乌托邦。真在乌托邦里住久了,人也会烦闷,照样会抱怨”,这是不是你对于“乌托邦”的解构?请谈一谈,“乌托邦”在你这里还存在吗?
魏微:乌托邦不存在。1990年代可能也没小说里写得那么好。我写1990年代的时候,写得还是蛮开心的,我自己写得很嗨。因为那是田庄的青年时代,也是我的青年时代。但事实上,我真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多好,就像每个人在度过自己青春期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有多好,只有当老去回望的时候,才觉得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有多么好,身处其中是不觉得的。所以我觉得美好的时光都是用来回望的。这个小说我写得最开心的一节就是1990年代,但真正我的肉身在1990年代的时候,也还是有很多迷茫、痛苦,也没觉得时代有多么光亮,只有当现在回望的时候,由于它整个跟我的青春期在一起、跟田庄的青春期在一起,才觉得那时候还是很好的,活力四射。
答读者问
A
魏微老师好!我们看到田庄只是一个普通人,她的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写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出生入死”,对于作家来说有什么趣味可言?你试图为当代文学殿堂增添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魏微:我希望田庄能够进入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成为一个别致的文学形象。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资格,如果没有资格的话,也许是因为我写得还不够好。但田庄,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还是比较别致的,她是一个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她跟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不一样。女性眼里的女性,女作家所写的女性可能会更接近于真实。我没有美化田庄,当然也不舍得丑化她,就是写出她作为女人的一些普遍特点。我觉得田庄这样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她身上的独立性和她在男女关系上的那种迷糊都还是比较别致的。不能说这个特性是大部分女性的特点,至少一部分女性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她还是很别致的。
B
了解到你在创作《烟霞里》之前,把《围城》和《红楼梦》又翻出来汲取灵感与力量。你是怎么样从这两本书中去获取一些可以与现实经验相联系的东西呢?如何在经典之中获取创作的智慧呢?
魏微:《围城》和《红楼梦》都是我很喜欢的小说,放在手边每年都要翻一翻的。这两部小说虽然风格不一样,但它们通过写人物关系来展现人物性格这一点对我写《烟霞里》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写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小说的语调一下子就有很多诙谐的感觉,可能是受到了《围城》的影响,那个调子就出来了。
C
《烟霞里》中,请问魏微老师怎么看田庄父母月华、家明这一对CP的情感关系?
魏微:田庄的父母,家明、月华,樊晓哲老师说这是一对CP,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对夫妻可能在中国的夫妻关系里也是比较典型的,属于女的貌似强悍,喜欢把控一切,男的就一路退到底,让让让,这样的关系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尤其是因为田庄的父母都是40后、50后的人,还是很有代表性。总的来说,我觉得情感关系里,尤其是夫妻关系里,如果妻子这方特别强大的话,对于孩子的性格会有影响,中国古话叫做母强子弱,我觉得用在孙月华身上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一对夫妻关系里妻子之所以那么强悍,可能也跟田家明一路让让让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夫妻关系是一种平衡关系,这对夫妻是没有平衡好。
D
《烟霞里》引入了许多“报纸新闻体”的转述,这样非虚构部件的引入无疑为编年史式写作的真实感添砖加瓦。在叙写时代的脉搏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魏微:《烟霞里》在非虚构这一块,对于大时代的描述用了新闻报纸摘要这样一个文体。写大时代小人物,我一直游走于这两极之间,对我来说其实非常有挑战性。我不认为自己做得多么好,后来因为篇幅的关系会觉得自己捉襟见肘,但在有限的篇幅里我觉得是尽力了。这还是一部很有挑战性的写作,经验方面我估计也分享不出更多的,反正就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写。
E
很多时候,长篇小说中写时代、历史都是“隐着写”的,重大的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藏在人物的行动背后。但在《烟霞里》中,时代和历史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它们架构起了这个小说整体的时间框架。这样的写法有利有弊,请魏微老师谈谈在这方面的考虑。
魏微:时代、历史现在小说里是一个显性的存在,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在大和小的方面我存在着一个艰难的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的笔墨有时候会有凌乱,会顾此失彼,但我的确尽了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好这样的平衡。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周佩文 实习生 陈灵君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作家魏微:《烟霞里》写故乡,也写都市人身上的“游离”
魏微《烟霞里》: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直接对话
魏微谈新作《烟霞里》:写作必须真诚,字里行间见生命
2023当代文学论坛|魏微:我写小说就是为普通人立传
《烟霞里》:编年体与时代之书
魏微: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赋予“霞光”
专家热议魏微新作《烟霞里》:拓展了广东女性文学的艺术疆域
小说《烟霞里》:县城青年走向城市
4·23世界读书日特刊丨魏微:“读书首先是自我愉悦”
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7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79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7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9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34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