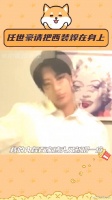好的小说家能睁着眼睛走进地狱,看到光
原标题:好的小说家能睁着眼睛走进地狱,看到光

当“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成为网络流行语,讽刺世界也讽刺自己的同时,也引出了“草台班子”上人们普遍的表演性。生活中每个人都在“演”——什么时候的表演是有意的,而什么时候的表演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作家陆茵茵好奇着,写下了小说集《表演者》。
一月初,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的新书分享会上,陆茵茵,《上海文化》杂志编辑张定浩,作家、译者和艺术评论人 btr 一起聊了聊我们生活中的“表演”,还有小说不同叙事方式的差异,以及《表演者》这本书中悄悄蕴含的“始终开始的力量”——“他们看到一个东西破碎,或者自己破碎之后,会等待照进来的光,希望光把裂缝弥合,把碎片重新塑造成一个新的人”。
以下是本场分享会的文字回顾。

活动现场,左起为张定浩、陆茵茵与 btr。
我对“真我”和人际交往中的“烟雾”感兴趣
Btr 《表演者》那一篇里,粗枝大叶的小姑娘叫“阔叶草”,崇拜她的男生叫“崇哥”,另外一篇里还有一个旅游社的老头叫“管老头”……你是想通过名字暗示读者什么吗?
陆茵茵 其实在我上一本小说集《台风天》里,很多人是没有名字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太知道要给一个人物取什么名字,另一方面,其实我是想写一类人——如果给人物一个固定的名字,他好像就被局限在一种个人经验里。
但我这次写作时,会觉得不取名字让我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很模糊,虽然那是我想要的一种削减,但它好像也会变得比较模式化。我还是想把它往稍微更有故事感、戏剧化的方向拉,所以就给他们取名字了。
“崇哥”和“管老头”这两个名字没有暗示,只是巧合。至于“阔叶草”,因为她和男主角是在社交平台认识的,所以我想给她取一个网名。取名的过程也很随机,是我爸爸一个朋友的网名叫“阔叶草”,某天正好聊到,我就觉得这名字挺好的,拿来用一下。
Btr 似乎“表演性”不是一个当代人才有的东西,是贯穿在人类历史中,非常普遍的东西,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贯穿了这样一种表演性。你怎么看待这些人物意识中的表演?什么契机让你想写这些东西?
陆茵茵 我对人的表演性很感兴趣。我们平时说“这个人在演戏”,会觉得他是有意识的,但其实很多是无意识的,比如《表演者》这一篇的男主角阿全,他是后来自己进入了跟他前女友阔叶草在恋爱中相似的情境时,才发现他好像也是在通过表演索取爱意。日常生活中,我们什么时候是想通过表演来获取一些东西,而什么时候又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模糊特别吸引我。我想知道这种模糊是为什么,以及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表演。有的时候我也会思考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这样做是想获取什么吗?我能不能不这样做?
我觉得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很多部分有一种烟雾的感觉。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跟别人的“真我”进行交往和碰撞的,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触及不到这个人的“真我”,甚至有的时候他都触及不到真实的自己。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有时他是有意识的,知道这样做并不代表我真正的态度,这不是“真我”;但有时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但在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这样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对所谓的“真我”和那层烟雾很感兴趣,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写了这些小说。
张定浩 表演其实是让人不安的。我们能够接受的表演,是在大家默认为舞台的空间进行表演,如果在生活中的其他空间遇到人在“表演”,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人跟我不一样,对我产生了冒犯。但我觉得,这种被冒犯的感觉其实是每个人自己要克服的东西,因为对于表演者来讲,如果始终有在舞台上的感觉,那时的自我其实会比“真我”表现得更好。我觉得真实的自我并不重要,因为大家真实的自我可能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是后天表演的不同——每个人对你的愿望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什么……是这些东西让你跟别人不一样,让你最后能绽放出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表演出来的。
你在表演中获得了一个比自己本身的人格更好的人格,那你当然要这么表演;但假如你出于一个很猥琐的目的去表演,这可能会让你的人格变得更差。我看这本书里面很多表演是出于爱——因为爱,他们才表演。不管是母亲对小孩,还是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那些表演都是出于爱。在这样的表演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对自己变得更好的期待,这是特别打动人的。
关于《表演者》这一篇,我再补充一点。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可以理解别人的经历,但很难感同身受,就像阿全,当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了阔叶草是出于爱他的目的“表演”,但他没法接受,直到有一天,当他处于相似的情境时,他才真的意识到这点。大部分人必须在自己亲身经历一个事情后,才能够真的体会。

电影《伪装》
小说家可能要做的,就是替很多人生活,让每个人通过阅读他的小说,一次一次地体验别人的生活,感受到自己在生活中感受不到的东西。
Btr 突然想到最近的一句流行语“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我觉得这句话就暗含了很多跟表演相关的东西。在世界这个草台班子上,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地扮演社会或者家庭给予他的一种身份。书中的那篇《三年级》,讲的是小学生中一个“大队长”的故事——我觉得“大队长”可能就是人在小时候会扮演的一种角色。
表演的复杂性贯穿全书。《表演者》那篇里有这样一段:阔叶草失控的时候,阿全突然意识她那种拿着刀指着人的悲怆,本身也是一种表演。陆茵茵接着这么写:“这失控恰恰在精准的控制之中。”我觉得陆茵茵的小说有一种心理分析的感觉,她是在讲故事,但不时地会像一个心理分析师,去分析人物的动机。人物在什么时候表演?因为什么表演?表演有怎样的特质?她把写小说作为一种进一步洞察世界,或者说去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非常有意思。
好的语言像强酸一样,
去掉人们的表演性
Btr 整本书 12 篇,你们最喜欢哪一篇?
张定浩 我最喜欢《金》,这篇讲的是“我”偶然看到了从前同事“金”的博客。我在里面看到了博客的一种表演性,以前大家写长博客的时候,会知道有很多的陌生人在看,就像在公开场合写日志,其实是有一点表演性的。但慢慢地,这个博客没人看了,它的表演性就会变少,流露出一些真的东西。
这篇有一段话,我觉得跟写作者的关系蛮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写作者自己对写作的一些态度。我觉得很多小说家对自己小说的认识都比评论家更准确——其实好的小说家都是自己小说的好的评论者。
那段话是这样的:“这样的句子。仿佛浸入强酸,把语言表面的狂欢和不自觉的伪装都蚀去,窥视到那颗心。”好的语言就像强酸一样,把表面的表演性都去掉,然后让你看到人物的“真我”。这是我读陆茵茵小说的快感,我仿佛像一个窥探者,跟着叙事者一起,窥探这些普通男女的内心,这也是为什么她的小说没有很强的戏剧性,但能吸引我看下去的原因。
Btr 我最喜欢《地下室》。这篇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女孩要离开北京回老家,就把自己的很多物件存放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整理的时候勾起了很多回忆。因为疫情,时隔几年她才又回到地下室。这里面讲到很多东西,有一个是陆茵茵写的“流水般的失去感”——那种“流水般的失去感”在这篇中特别明显。还有一些空间上的安排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这篇里面光线的变化。
另外,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关于人、物件和记忆之间复杂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物件的世界里面,这篇讲了很多物件是怎么勾起回忆的。人怎么对待物件,似乎就是怎么对待回忆。

电影《伯纳黛特你去了哪》
我也挺喜欢《心之碎片》的。这篇描述了一种,用陆茵茵的原话是“一切都悬荡起来的静默”,讲了一个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的故事。
《心之碎片》里面,陆茵茵写里面的人“要用具体的句子让抽象的感觉现形”,我觉得跟刚刚说的“强酸性”的目的是一样的。“强酸性”是去除真实上面的遮蔽;“要用具体的句子让抽象的感觉现形”是想从一个雾障中呈现什么——它们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显现一些东西。
陆茵茵 《金》好像是我第一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写《台风天》的时候,我都是用第三人称,没用过第一人称。我觉得用第三人称是非常自然的写法,好像隔着一段距离,于是可以非常冷静地写。写《金》的时候,我是有意识地想试试用第一人称写。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危险——用第一人称的时候,好像把一部分的自己注入了这个“我”当中,但它肯定又有虚构的部分。虚实夹杂,你怎么把控其中真实部分的比例?
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发现跟用第三人称写完全不一样,好像一个我认识,但又很不熟悉的人在讲话,她的语调和以前非常不一样,我就会有一种失控感。我是一个有点害怕失控的人,喜欢事情井然有序,但失控感又莫名地吸引我。她好像有很多要喷涌出来的话语,但我不能让她就这么全说出来对吧?有的时候我还要删掉一点,反正就是要一直调试——《金》就是第一篇这样写完的小说。所以它,以及其他很多我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里面,还是有我觉得很陌生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以后还是会继续用第一人称写写看的。
《地下室》也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记得很清楚,写完地下室之后,我觉得接下来要用第三人称写,回到熟悉的维度,所以写了《心之碎片》。《心之碎片》的写法是我相对熟悉的,写的时候我感觉很安全,也更容易。
整本书里面有一半的篇目我都蛮喜欢的,不过作为作者,也不能说什么喜欢这篇,不喜欢那篇——我写每一篇的时候肯定都会学到东西。但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蛮喜欢《安迪哇猴儿》《表演者》《SUCK U》《地下室》《心之碎片》《三年级》的。
张定浩 初学者写小说往往喜欢用第三人称,但其实是在用第一人称——小说里某个主人公仍然是他自己。他戴了个面具,以为别人不知道那是他,他反而会更加自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太能发展自我的。
而用第一人称写时,写作者会意识到失控。这种失控会让他变得跟原来的自己不一样,慢慢地控制住失控的自己时,就会成长。
这些年第一人称写作其实蛮流行的,比如去年获奖的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再之前的塞巴尔德的作品,还有我很喜欢的乌格雷西奇,一位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荷兰裔作家,她的小说《狐狸》也是。第一人称写作的自由感就是可以把虚构和非虚构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叙事者的我会得到扩展,得到丰富。第一人称写作也很容易产生一种跟着主人公一起的代入感。这些都是它迷人的地方。当陆茵茵采用第一人称时,恰恰比第三人称更能带读者逼近那些类型化的普通人。
好的小说家能睁着眼睛走进地狱,
看到光
张定浩 我觉得《心之碎片》很有代表性,甚至说陆茵茵的小说都在写某种心之碎片——人物处在破碎的状态中,通过积极地表演,一点点地把碎片拢聚起来,让自我恢复健全。
我觉得这个过程蛮动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陆茵茵的小说和很多同时代的写失败者的小说不同。我上次听一个批评家说为什么现在有些小说那么火,因为它们都是失败者之歌,在一个下坡的时代,很丧的时代,你失败就很容易打动人,但我不太看这种小说。
我觉得在小说里,把失败当作一个起点是可以的,但不能把失败当作最后跟大家谋取某种“合一”的地方。陆茵茵的小说里面始终有一种肯定性,就像《金》里面,上海以前很多男性会到日本洗盘子打工,“我”的父亲可能是其中的一员,但父亲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一个到日本洗盘子的人,而是有更多正面的东西。当“我”和很久没见的父亲在公园里玩时,说了一句:“我喜欢迎着太阳,不躲不藏。”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我觉得陆茵茵的小说经常在一些平常的隐喻中,体现人生某种肯定性的真相。
这种肯定性特别重要。《大都会》那一篇,也是关于一个人破碎之后如何重建——换掉手机,租房子,重新一个人生活。这些破碎的人感官仍然健全,在小说里不停地看、拼、嗅,依旧在努力地跟外在世界接触。他们并不是天天顾影自怜,有各种各样的外界信息向他涌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慢慢恢复的前提——你要对这个世界感兴趣。你可能遭遇某种变故,但你要用一种对世界有兴趣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
还有一点,我记得《心之碎片》里面写到一个父亲,“他一直努力扮演父亲”。我前阵子在杭州见到一个业余演员,他跟我说他之前在北京做了几个月快递员,觉得这个工作很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个暂时的工作,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快递员,所以他能接受快递员这个工作带给他的所有困局——他知道这会结束的。
其实我们人生中的一些阶段也是会很快结束的。我那天就开玩笑,说我天天在家跟我女儿大呼小叫,看了陆茵茵这本书之后,我以后就想象自己是在扮演一个父亲,我就扮演个三四年,很快的。等女儿考上大学了,我对这个角色的扮演就结束了,就可以不管了。我觉得这样想的话我会心平气和很多,不会觉得这个日子都没法过了。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里有这样一句,“世界是一座舞台”,周星驰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舞台。
陆茵茵 “我喜欢迎着太阳,不躲不藏”这句话真的是我爸说的。有一次我跟他走在路上,他突然就用上海话说了这么一句。我当时觉得好奇怪,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其实他就是想说,他不喜欢撑伞或者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他就喜欢迎着太阳,哪怕是大太阳,他也要走在路上,让太阳照着自己。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很文学,我爸爸会突然说这么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就把它记下来了,用到了小说里面。

电影《杨之后》
在“失败”这件事上,我觉得大家的感受不太一样。其实我是认为没有什么失败者的,我更看重一个人内心的发展。我不觉得一个人的外在失败了,内在就一定也失败了。人在失败的时候可能会得到更多东西,那些东西不是外在的,而是关于他怎么熬过这段失败的,比如变得更有韧性,更有承受力了。这些都是不能靠外在的东西来评判的,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个人的失败,都是经历。
我感觉我不太会去站在一个所谓的失败者的立场写小人物。我觉得没有“小人物”和“大人物”,都是普通人,都是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走自己的路就好了。你不说我都没意识到这是一种肯定性,确实是这样的。
Btr 书里很多写的都是非常日常的生活,好几篇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是值得书写的?
陆茵茵 我想写别人可能没有写过,或者很少写的一种东西。大家都去写肉眼可见的存在,写我看见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很戏剧化的事情。于是我想,如果我写“没有”呢?就是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可不可以写?我对不太被人描述的感情、情绪、感觉,比较有兴趣。我在这儿等,你还没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为什么我心里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心之碎片》这篇里的感觉。
Btr 张定浩觉得陆茵茵和其他当代华语写作的差别是什么?陆茵茵特别在哪里?
张定浩 陆茵茵主要选择写“无”,写“无”的前提是你有写“有”的能力。很多小说家可能是不太会写对话,就在一个人的意识流里面,不停地交代情节,不停地交代故事,缺少可以听到别人声音的“耳朵”。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小说家很重要的能力。
陆茵茵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她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但她某段时间选择了写“无”,而不是写这些声音。有能力但不去写,这和那些故意写意识流的小说家是不一样的。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部小说里,主人公“睁着眼睛”看着事情发生,可以说他是睁着眼睛走进地狱的。小说家要非常强悍,才能一直睁着眼睛看所有的事情。《心之碎片》这篇是讲两个女孩的聊天,她们以前是同事,现在偶尔见面聊天。她们聊天的内容是其中的一个女孩暴露自己的伤口,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安慰她,只有这样,这个聊天才可以继续下去。有一次,那个暴露伤口的女孩当天挺开心的,就不太想聊她的伤口了,于是聊天进行不下去了。为了让聊天进行下去,她又主动提到了自己的伤口。这其实就有一种睁着眼睛走进地狱的感觉——她其实意识到了所有的东西,仍然目睹它,不躲藏,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说到碎片,碎片意味裂缝,我很喜欢莱昂纳德·科恩,他有一句话:“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我觉得陆茵茵小说里的人物等待的就是这种状况,他们看到一个东西破碎,或者自己破碎之后,会等待照进来的光,希望光把裂缝弥合,把碎片重新塑造成一个新的人。这里面有一种始终开始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力量是贯穿于很多小说的主题。好的小说家都有一个长期的主题,比如村上春树,他说过自己的小说主题是,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某种东西,往往都无法追求到,即使追求到,珍贵的东西可能也受到了某种损坏,虽然如此,他必须这样追求下去,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这有点像西方文学里面一个古老的主题——寻找圣杯。可能陆茵茵这里也有类似的主题,不一定是寻找某样东西,但就是重新开始,在碎片当中重新开始,等待某种光照到裂缝里面去。
《地下室》这篇最后也提到光,某一刻,光也会照到地下室里面去,那种东西是很动人的。我想到韩国电影《燃烧》,小小的房子里,只有一瞬间光可以照进来,即使是从对面的高楼通过反射照进来的光。小说家要看到光,他的写作才有意义。

电影《燃烧》
▼
等待光照进我们心的裂缝
《表演者》签名本现货发售中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眼睛好清澈的一姑娘
《光精灵的眼睛之旅》:用艺术之美做眼睛科普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没人能拒绝杨幂的眼睛
苏州吴中作家走进光福创作采风活动举办
韩东:好的小说家、好的随笔作家甚至好的导演,都应该是诗人
岳不群看到令狐冲使用的剑法,立马眼睛都亮啦
霍启刚带郭晶晶与儿女看球赛 女儿大眼睛水灵儿子独立懂事
十八层地狱里都有什么?下地狱的规则,可能人人都无法逃脱
猪:这就是地狱吧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66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6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27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