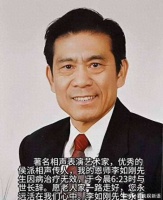葛亮:饮食是可复刻的文化密码,与记忆和历史相连 | 文艺青年的101种活法No.38
原标题:葛亮:饮食是可复刻的文化密码,与记忆和历史相连 | 文艺青年的101种活法No.38
“既是日常盛宴,也是冷暖人间”,近日,继《北鸢》《朱雀》后,作家葛亮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燕食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燕食记》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搜狐文化对话葛亮,当他谈及文学的各个切片,种种思考亦仿如文火慢煮,深沉又清鲜。
葛亮
“三餐惹味处,半部岭南史”,岭南饮食体现着文化的流动、开放和自由感
搜狐文化:您在新书《燕食记》里面写到,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很久了,大致是从《北鸢》的时候开始的?
葛亮著 《燕食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葛亮:对,因为读者朋友们都能够感觉到,在以往的长篇写作,甚至是我的一些短篇幅的作品里面,也会出现有关于饮食的意象。写这样的一本作品也是我内心中间的一个夙愿。我觉得饮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的意象,实际上它像那种很有意味的历史的密码。
我相信每一个写作者在他的写作初期都需要寻找某种情感的落点。就我的几个长篇来说,《朱雀》因为有关于我的家城,所以它的写作背后埋藏着浓浓的乡情。《北鸢》因为相关于我的家族,我相信亲情是创作层面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我本人在岭南已经生活了 20 多年的时间,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会有一种创作的想法和意念,用这个小说来回馈这方热土。饮食恰好也是有关于岭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切片。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广东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是最能够体现岭南文化的气韵的,恰恰就是饮食。
岭南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它有非常独特的一种气性,就是它的海纳百川,包括它的一种流动性、开放性乃至一种自由感。饮食在这个角度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地域体现出来文化的融合,自身的一种薪传以及递变的过程。所以它不仅仅只是我们的日常所需,它更多地也体现出有关于历史文化的肌理深处的可以被我们所截取的一种文化密码。它可以被复刻,同时也可以定义我们的人生乃至于记忆,甚而是定格某一个时代以及历史的节点。
就《燕食记》这部小说的形式而言,我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我希望借由这个文本去体现某种在文学深处的一种对话性,就是一个当下的人如何和他对望的历史之间产生一种砥砺思辨乃至于相互之间融通的关联。这也构成了这个小说有关于非虚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复调。
搜狐文化:比如说从南京,到香港,再到岭南,您可能更多地写作长篇的这种系列讲的是一个流动的传统。您自己会反对地域化的标签吗?
葛亮: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的长篇写作的一个脉络,它肯定还是有一种在地理上的考量,无论是《朱雀》里面所写到的江南,《北鸢》里面体现出来的中原,还是《燕食记》所呈现的岭南。我相信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幅员辽阔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它体现出来一种在地理和文化品性上的一种多样性。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不断去挖掘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其实也是一个写作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去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本身必须要探讨的一个内容。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有关于文化的这种流转,恰恰也是在《燕食记》这部作品当中,我想去表达或者跟读者之间分享的内容。因为刚才也提到岭南文化,它这种气性是建基于一种海洋性的文化,所以它体现出一种海纳百川的特征,这里面也造就了一系列相遇。所以这个小说中间实际上有大量的不同人群之间在相遇的基础上交融砥砺,同时也产生了有关于文化的一种变体。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岭南文化特别吸引我的地方。而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表现这样的相遇或者文化的变体所出现的土壤。
叙事链条中的“我”,随着历史变迁而变化
搜狐文化:您日常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样的?
葛亮:因为我本身在大学里面执教,就写作习惯而言,也是依循于我平常生活的规律。所以我的长篇写作和中短篇写作的周期其实是不一样的。在学习中课业比较忙碌的时候,可能是中短篇居多,大块的假期时间可能会用于我的长篇,所以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衔接和融通。我觉得在两个大块时间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其实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更加地利于你对之前所写下的内容做一些回望和沉淀,这个时候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表达,无论是审美还是叙事上的更加准确。
搜狐文化:您提到在大学里面然后也会去做文化相关的项目,从一个学术的角度,做项目会更多偏田野调查和社会学的方法,跟文学创作有所不同。您自身有创作者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在这中间您会不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葛亮:就我自己的创作经验而言,我希望这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因为你提到的田野考察的部分,甚至于案头的部分,资料查考的部分,它同时也是我在做文化乃至于文学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必备的一些学术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研究的方法纳入到这种大体量小说前期的准备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同时这种训练的过程也带来了对于历史思辨的一种延展性,乃至于对于文学结构架设的逻辑感的锻炼。所以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做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也得益于此。反之,因为创作实践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转而进行文学研究的这样一个脉络中间,会更加能够让自己将心比心。
搜狐文化:在您的作品构建中,我们能够看到古意,同时又是非常当代的。您是怎么把非虚构的史料用在文学创作中的?
葛亮:这也是涉及到一种对话感。我希望一个长篇小说,特别是有关于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能表达出我们当下与过去的一种对话感。包括我自己这几部长篇,其实叙述者的声音也一直在变化。比方说在《朱雀》里面,因为当时我本身是一个青年的写作者,所以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对于历史的判断上,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当下人的一种角度的发言,当时的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北鸢》的时候,因为是有关我的家族,更多的其实我希望让历史本身来说。所以这个叙事者往往是实际上是埋藏在整个的这个文本铺设之下的。但是在《燕食记》这个作品里面,我更加想体现出就是一个当下的人,他带着当下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去怎样谛视历史。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不是单向的,历史也会给予它一种回馈。所以整个的叙事链条中“我”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和历史的关系也一直在变化,他从前期和历史之间的这种砥砺,甚至于在一种质疑的这种阶段,他在发出自己的某种声音。但在后期,他越来越和历史之间产生一种相濡以沫,甚而是同声相和的状态。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犹如镜像的角色,进入到历史脉络的过程,同时也映照出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特别是当下的写作者对于历史的一种感知。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传统深处最有意味的就是它有那种基因一样的,焕发出不同的面相或者说是可能性。它既可以除旧布新,也可以推陈出新,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时刻使我们在看待历史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活的状态。历史本身实际上也是充满了活力的,可以和我们当下人进行对话的。
搜狐文化:读您的著作,脑海中会浮现很多具体的画面,比如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想知道您在写作的时候,脑海里有没有一种画面感?比如说传统的中国风俗画或是电影的画面感。还是说您的写作架构是完全文字的、理性的,或者是二者并存的?
侯孝贤导演《海上花》(1998)
葛亮:首先我在长篇小说写作的层面,我还是蛮重视有关于细节的铺设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对于在场感,还是整个的历史线索的铺陈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因为其实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共情和共鸣恰恰就是来自于这样的细节的呈现。
有关于场景感的部分,一定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要去考虑的范畴之一。这也是相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话题,在前面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的。食物它作为一种切入点,它也埋藏着一种日常的气象。这个日常的气象可以是连接的历史,同时也指向我们的当下。所以为什么我也说食物是一种可以被复刻的文化密码,因为它和我们的个人记忆往往是相联系的。
有关于节气,有关于我们的礼仪,有关于风俗,其实都能看到食物的印记,我们端午要吃粽子,我们中秋要吃月饼,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文化习惯被食物所定义的这样一种特点。我们的一生从刚出生的时候摆满月酒,到后来的在嫁娶的过程中吃喜饼,乃至于到了人终结了自己的一生,我们也会在丧仪上喝豆腐汤。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过程中间,我们所谓的舌上之味已经铭刻于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种历史日常的肌理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关于场景感的部分,在这个小说的整个的这种写作过程当中,也成为了我去表达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
文学历经沉淀,长篇小说包裹起我们的生活观
搜狐文化:因为长篇小说还是很适合改编后搬上荧幕的,比如说像《燕食记》出版之后,有没有人想要把它影视化?您对这种影视化改编会有怎样的想象或偏好吗?
葛亮:就这点而言,我是觉得尊重不同的艺术它的一个自身成长的规律。因为我在学院里面不但是只教文学的课程,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也是关于电影,其实这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艺术形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小说的原著者,可能更多的会关心的部分恰恰在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尊重,我不会对它进行太多的一种拘囿。
从另外的一个层面上来说,关于这个小说创作在改编上的一些意向,这一点我觉得心态可以更加的开放。因为有不同的人来演绎,有不同的艺术家去表达呈现出来的影像化的状态,可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我恰恰觉得呈现出一个艺术创作的一种多样性,而不是我们想象中一种唯一的表达。就像我们每个人其实对于食物的体验也不一样。同样一个食物,我们吃下去之后,有的人会即刻感受到它在味蕾上带来的刺激,有的人可能会体味到一种回味绵长。这是跟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和阅历都有关联的,有的人可能会激起自己内心中间的乡情,而有的人可能更关注于当下。
搜狐文化:我们谈到您关于文学的日常、教学和影视化,文学在原来可能是一个必需品,但是现在除了喜欢或者是文学专业的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会觉得必须要读诗,或者说我必须得去小说、文学作品中寻找一些解药。您怎么看待文学在当下的意义?
葛亮:我觉得首先文学它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或者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意义,还是说它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共情,甚而是一种感动,这点还是十分的重要的。
如果说到我与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文学还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的。那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想象和再生以及去演绎的空间。这和影像还不一样,因为影像带有某种唯一性,当然你可以再通过影像去验证你的文学想象,但两者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从另外一点来说,我们会觉得文学似乎和所谓的这种日常生活中间存在某种壁垒,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文学其实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某种映照,这实际上是一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信息传导的路径在发生极大的变化,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甚而是获取信息的这种频率也越来越密集。但是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沉淀,沉淀之后使得我们做一个当代的人,不急于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仓促地做出判断。
我觉得这个是文学的意义,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经过了思考的艺术,经过了一种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它同时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非常有机的一种整理甚而是提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反而觉得文学对于当下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会越来越大。
而且我觉得文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艺术形态的一种优势,就是它对我们会有一种唤起、唤醒的作用。比方说就历史而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生活观其实里面是内藏着历史观的。但是由于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它是一种绵长的一种状态,它实际上是对我们当下的生活观产生了一种包裹的作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历史中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未来。而当下其他的介质或者是平台向我们所展现出来的信息,它的这种密度是够大的,但是它的质地是否是在一种一蹴而就的形态之下,就能够表现出它精准的定位,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文学和我们的脑回路之间,存在一种同奏共振的关联,所以它是陪伴着我们的思考的,而这种思考一定是相对比较深入的。
文/刘奇奇 视频/张妮 审/任慧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作家葛亮:以《燕食记》写出岭南地区鲜明的文化气象
标·本:康青的植物记 | 文艺青年的101种活法No.36
看不见的城市:徐明松的手机微摄影 | 文艺青年的101种活法No.35
蔡东葛亮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办剧院、做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数字藏品演绎“中轴线上的历史回响”
成都“小酒馆”,从文艺钉子户到文化创意样板街区操盘手
记忆与爱,随《受命》重回八十年代北京
尊重历史是古装片的压舱石
“文学交流能为两岸青年提供精神力量”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7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0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