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副架子展现一位父亲的命运
我为何选择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的微型小说《木棍》(取自《十二月十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来讨论?并非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以及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而是《木棍》符合他的小说观念和我对微型小说的看法。所谓“作家中的作家”,通常是后人公认的能够启发作家的经典作家,就是作家们的“先驱”或“师傅”,而且引领了流派或风格。但我倾向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作家中的作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给予了启示的作家:小说还能那样写。并且,一个作家在创作的路途中,总会遭遇创作的瓶颈、疑难、迷失,因此,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作家中的作家”。我心目中的“作家中的作家”是:卡夫卡、契诃夫、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因为他们的作品我常读常新,经得住重读,能解惑释疑,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石”。桑德斯选择了俄罗斯四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在创意写作课上(他是美国一所大学创意写作的教授)作为“范本”讲解,也显示出他的“作家中的作家”。
回到选择《木棍》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2014年5月时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月十日》,同年9月2日重读,对《木棍》印象颇深。我做了笔记:“写父亲的小说甚多,怎样写出父亲这个形象的独特性?桑德斯给父亲配套了一个贯穿全篇的细节:架子。采取聚焦的方式,写父亲就写架子,而写架子却写棍子——木棍是千余字的微型小说的高潮和亮点。小说,顾名思义,要往‘小’里‘说’,以小见大。而微型小说,比‘小’了还要‘小’,细节决定成败,本以为题目该用《架子》,但是,桑德斯却以仅出现一次的木棍为题,架子明摆着,棍子亦被忽视。由此,暗示此作的力量所在,属于点睛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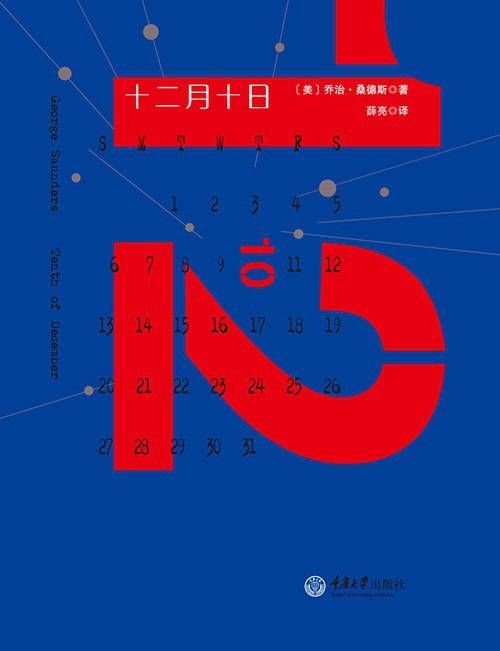
《十二月十日》
理由二,2024年11月11日读毕桑德斯的小说系列评论《漫游在雨中池塘》——关于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四位俄罗斯19世纪文学大师七篇小说的七堂讲座,我看到他透视了经典小说内在的微妙。桑德斯敬重大师,但他也回避了19世纪小说和21世纪小说即传统与当代小说的区别,正是心理描写。四位大师的小说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主与仆》,在这个关于迷路的故事里,小说的心理描写构成戏剧化。桑德斯在分析时则强调行动的重要性,他在解析屠格涅夫的小说《歌手》时,借用亨利·詹姆斯和纳博科夫的话,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缺乏戏剧性,由此引出他自己的小说观念:“我们目前的审美理解是,人物的描述应当快速、自然、有序地表现在行为中,我们相信人物的特征是展现出来的。而不是讲述出来的。”在此,桑德斯强调了“行为”,其实传统与当代小说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世界观,19世纪小说用的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视角,而当今的小说视角降低,不可知不可料,用行动描述代替心理描写。桑德斯讲到《主与仆》中晾衣绳的细节,衣物递减与心灵的升华(桑德斯称为升级)之间的关联,让我想到了《木棍》。我不知桑德斯写《木棍》和讲述晾衣绳,是否构成了隐秘的关联,但显然两者间有异曲同工之妙,桑德斯的《木棍》里可感受到经典的回响。
桑德斯在讲座时不经意的两句话:“来吧,有趣点儿”(“有趣”即细节的有趣的意味),“反应才重要”(在分析果戈理的《鼻子》时,他强调“故事中出现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实不在于事件的发生,而在于对不可能事件的反应”)。且看《木棍》里的有趣和反应、变化和升华所构成的故事。
显然,《木棍》里没有读者期待的强戏剧性,这也是当今作家面临的考验:没有戏剧性的故事该怎么写?而且要“不一样”。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也是变化的艺术。《木棍》中,人物的命运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变化,桑德斯处理时间,大时间模糊——“每年”“有一年”“有一次”“后来有时”“有一年秋天”“到了冬天”等,均不点出是哪一年;小时间明确——“感恩节之夜”“超级杯决赛的那个星期”“七月四日国庆节”“生日派对”“智利地震”“妈妈去世”“父亲去世”,时间貌似具体,却剥离了“大时间”,定格为“我们”和“我”永恒的记忆碎片,时间的流逝和转换中,携卷着人物的命运。
如果把每一个片段视为一个情节的话,那么不构成我们通常所谓的戏剧化,只仿佛是碎片的拼接。而叙述的一个个碎片,第一人称(先是复数,后为单数,也显示出作为孩子们的“我们”的分离、成长史)冷静、客观,有着不露感情的冷漠,正如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的女友问:你爸那个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眨巴眼,无言以对。那是不可知不可料的低视角,至多做出反应,隐去了心理描写,只显现“行为”,让人琢磨不透。而且是“快速、自然、有序”的行为——父亲像表演魔术师般的“有趣”。但作为读者,我看见了行为背后丰富的心理。

《漫游在雨中池塘》
桑德斯给父亲这个人物配套了一个架子的细节,经历人间沧桑的父亲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同时间不同问题,在架子上装饰或置放不同的东西,架子就是父亲情感交流和表达的平台,挂上的物件是无声的语言,此时无声胜有声,尤其有“光”,自带“光”。架子上物件的变化与父亲命运的变化密切相关。桑德斯将父亲和架子置于平等的地位,仿佛是关闭了音响的二人表演,“我们”这些孩子就是观众,渐渐只剩下“我”这个观众了。不妨细心留意每一次架子上物件的变化,就可以发现父亲是感情丰富、柔软细腻的人。只不过作为孩子,尚未产生共鸣和共情,那也是父亲的孤寂。结尾,父亲去世,架子也“死”,“我们”处理后事,卖掉了房子,拔起了架子,“在收垃圾的那天,把它摆放到路边”。
桑德斯是凭借那个架子把父亲与家人、与时代、与命运有机地组合起来。微型小说写人物命运自有独特的叙述策略,架子这个细节紧贴人物进行运动,家庭的变动、时代的节点、架子的挂件,这三条线与其说聚焦着父亲的命运,倒不如说父亲的衰退、孩子的成长,均由架子来贯穿。
然而,孤独的父亲赋予架子以灵性,这是桑德斯对物件的态度,同时也是他文学的发明,更关系到小说的升华(就是他所说的升级)。每一次架子变化,也是父亲心理的变化。“有一年秋天”父亲把架子涂成了晃眼的黄色,“到了冬天”又给架子裹上了棉球,给架子保暖,架子有了灵性。经典作家还会进一步“升级”(升华),竖起了六个小的十字架的木棍(父亲解说“是那个架子的孩子们”),再进深一步,父亲用绳子拴起架子和木棍,显然父亲有我们这六个孩子,并试图维系父子关系。桑德斯是一个有精神能量的作家(一般作家写到此就“乏力”,精神下滑、下坡),而他继续往人物心灵掘进:父亲把“一封封道歉信、认错信、恳求信用胶布粘在那些绳子上”,往深里挺进一步:父亲画了一个代表爱心的牌子,挂在架子上,还画了另一个牌子:“原谅我好吗?”这是临终遗言。就这样,他的写作与19世纪忧伤的心理描写“不一样”了。
我想起有“教母”之称的日本作家向田邦子的《父亲的道歉信》的结尾处,父亲向女儿道歉,兜圈,委婉,仅仅在给亲戚的信中顺带一句对女儿迟来的道歉,而整篇都没有写道歉。对比东方和西方父亲的道歉方式,反差明显,与文化的习惯与行为的方式有关。但返回前面的片段,父亲凭借架子的“表演”,而孩子们缺乏应有的“反应”,热与冷的对比,父亲的道歉既显示了孤独、寂寞,也彰显了宽厚、包容。架子贯穿全篇,然而木棍表现了父亲的心理,仿佛捧出了一颗敞开着的慈父温暖的心。父亲孤寂到什么程度:死时还开着收音机。这与前面的片段呼应:父亲关心世界的变化。可见桑德斯用木棍为题,颇有深意,这是小说的闪亮之眼,这不也是经典作家与一般作家的重要差别吗?用架子为题是常规,而木棍则是提醒小说里的孩子们和作为读者的“我们”。
现在,我做个假设:打开每一个片段会怎样?每一个片段像一个小盒子,有时间,有事件。《木棍》中,每一个小盒子都合上了盖,要是打开盖子将事件舒展开来描述,那意味着有很多的可能性,也可以成为短篇、中篇了。不过,《木棍》的文本彰显了微型小说独特的叙述策略,并非短、中篇小说的浓缩,而是更简约的叙述,只是紧扣架子挂件的变化就富有叙述的节奏,传递出了行进的动态。父亲的一辈子和一个衣架子,以及叙述的“声音”,都凝结在了木棍上了,这正是小说的高潮处。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
相关知识
如何用一副架子展现一位父亲的命运
夜袭敌军,看志愿军战士如何用黑夜颠覆战局!
上任途中巧遇土匪,且看他如何用黑话机智脱险!
小雨突袭双选会?别急!来看她如何用一段话稳住全场!
消失的凶手:看高智商罪犯如何用最简单的工具完成越狱
原来粤语也可以这么甜!佘诗曼教你如何用粤语召唤对象
和我讲中文? 看老外如何用中文投诉外卖,笑不活了
如何用一个词儿形容天津人?听老天津人郭德纲怎么说
《娴聊》第五期丨对话安一宁:如何用自我诠释引发观众的共鸣?
女朋友想减肥?看尹峥如何用三句话打消李薇减肥念头!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47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43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44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588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04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24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67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37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2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