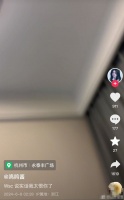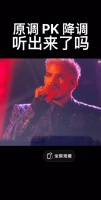何伟为《巴黎评论》采访他老师约翰·麦克菲的这篇访谈终于出版了
编者按:2013年,约翰·麦克菲的非虚构作品《控制自然》在中国首次出版,其中收录了何伟(彼得·海斯勒)写的推荐序《我的老师麦克菲》。其时正是何伟凭借《寻路中国》《江城》中文版的出版而在国内大火的时候,因此这篇序言也收获了颇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国内读者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知道了“约翰·麦克菲”这个名字——以及,作为一门专门课程的非虚构写作。也正是在那篇文章中,何伟提到了他受《巴黎评论》杂志委托采访恩师约翰·麦克菲的事,并援引了一些访谈段落,引发了中国读者对这篇访谈的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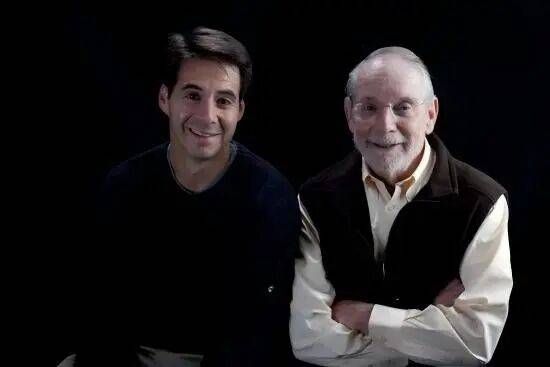
何伟与麦克菲
这次访谈发生于2010年,何伟时年41岁,约翰·麦克菲时年79岁。两人的交流持续了数天,且一大半交流都发生在普林斯顿大学麦克菲的办公室里。此时的何伟已凭借“中国三部曲”声名鹊起,但他在这篇访谈中表现出了足够的谦逊——在采访者手记部分列举麦克菲一些有名的学生时,他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
2026年,在这篇访谈于《巴黎评论》杂志发表近十六年之后,我们首次将其引入中文世界,收录在《巴黎评论·非虚构作家访谈》一书中正式出版。访谈译者李雪顺老师是何伟《江城》《寻路中国》《奇石》的译者,他同时也是约翰·麦克菲《写作这门手艺》的译者。

新书上市之际,我们特在此节选这篇访谈中的部分问答供大家试读。访谈完整版请见《巴黎评论·非虚构作家访谈》,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麦克菲
《巴黎评论》:你的毕业论文是一部小说。这在当时有何特别之处?
约翰·麦克菲:那是大学历史上的首创之一。是否应该允许我这么做,英语系有过激烈争论。他们最终决定,我可以照此进行,但也有反对声音。一个给我上课的教授在图书馆拦下我说道:“好吧,约翰尼,在那件事情上祝你好运。我相信你能赚到大钱。但我不会给你授予学位。”说完,他就顺着走廊离开了。
他们让我在进入四年级的第一天交出三万字。于是,我把自己一整个夏天都泡在燧石图书馆,待在英语研究生学习室里埋头苦干,在黄色的簿记纸上奋笔疾书。我那段时间是真的过得很爽,跟一群英语研究生并肩奋斗,全都处在不同阶段的煎熬之中。我写完了三万字,又在接下来的圣诞节期间完成了所有任务。文章的结构安排得确实不错,就技术层面而言堪称佳品。但其中完全没有生命力。其中一个人给文章贴的签子上写着:你让人看出,你已经会装马鞍了。好吧,现在就去找一匹马。
但写作要靠写来教。我给你这么说吧,就在我在燧石图书馆度过的那个夏天,我感觉自己明显地在朝着作家的方向成长。你不可能仅仅坐在那里写上三万字,结果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
我在大学期间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歌。不过,写得不行,真是不行。我是说,写得很烂。我就是这么发现的——写了才知道。我逐渐倾向的写作类型是纪实性写作。我从没有回想过其他类型的文体。我走对了路子,而我也热爱这种状态。不过,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总要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所徘徊,才能弄清楚自己要成为哪一类作家。
《巴黎评论》:你一直希望给《纽约客》写稿吗?
麦克菲:关于作家,罕有例外的一点是,他们的成长很缓慢,十分缓慢。约翰 · 厄普代克进展很快,他是个特例。这不是模式,只是一种现象。我读大学期间就在给《纽约客》投稿,此后过了十年,他们才开始接受我的有些东西。我曾经把他们写给我的退稿信用来贴墙壁。作家的发展很缓慢。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不要用望远镜的另一端打量我的职业。我是给作家,以及想从事写作的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巴黎评论》:你进入《纽约客》之前,在《时代周刊》度过了七年时间。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
麦克菲:《时代周刊》是我进行训练的地方。我在那里的七年,有五年是在娱乐部,娱乐部的作家比其他部要做更多的亲身采访。比如,有关杰基 · 格利森(Jackie Gleason)、理查德 · 伯顿(Richard Burton)的封面故事,全都是我做的报道。杰克 ·本尼(Jack Benny,美国喜剧演员,以其主演的广播电视喜剧《杰克·本尼秀》闻名)来到纽约后,我跟他坐上同一辆出租车,进行了一段采访。但如果是在外国事务部——当时就是这么叫的——从事写作,你就要根据驻外机构发回的材料进行创作。不管故事有多短小,单是每个星期要拿出五篇结构完整的报道这件事,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跟《纽约客》说上了话。我甚至卖了一篇短篇回忆文章给他们,但只跟一个编辑有过电话交谈,对在那里寻找未来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那篇文章本来是我给另一家杂志写的,差不多是偶然地投给了他们。但他们那里有个名叫莱奥·霍菲勒(Leo Hofeller)的家伙,人人都知道,他经常去贝尔蒙特公园打发时间。这个莱奥·霍菲勒呢,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有头衔。他是执行主编,主要工作就是到街上找人说话。他是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美国出版人,1952 年至 1987 年任《纽约客》主编)的“挡箭牌”——他的办公室就在肖恩的隔壁。莱奥 ·霍菲勒说,他打算让我小试牛刀。我能给“城中话题”栏目想出六个点子吗?我写了几篇样稿,然后送了过去。
《巴黎评论》:你还记得内容吗?
麦克菲:其中一篇写的是一个在纽约下东区种玉米的人。但至于某篇文章要不要编进杂志,我们并没有过任何讨论。接着,莱奥·霍菲勒给我打来电话,说让我过去一趟。这是一向出入于贝尔蒙特公园的莱奥·霍菲勒。这跟威廉 · 肖恩还一点都不沾边——他就一墙之隔,但你不可能见到他。我满怀激动地过去了,他坐下后说道,这几篇写得还不错。接着,他转过身又说道,我说的是还不错,不是特别的好!我坐在那里,抖得像一片杨树叶。随即,他告诉我,他希望我能就三篇稍长的文章说说想法。然后,他又说道,下次过来的时候,别再老拿那个篮球运动员说事了!我们刚刚报道过一个篮球运动员。
《巴黎评论》:比尔·布拉德利还在打球吗?
麦克菲:当时,布拉德利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打球。我对他非常着迷,不仅仅因为他能完成跳投,还因为他的经历十分有趣。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几年,对比尔的经历有很多了解,因为我父亲就是球队的医生。于是,我坐下来,给莱奥 ·霍菲勒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信。信的诸多内容都编进了《你明白自己所处》。我的意思是,《纽约客》上的报道有一万七千字,但那封信只有五千字,我可能从信中引用了三千字。我当时告诉他,我对这个主题十分痴迷,所以我要以自由撰稿的形式给别的人写这篇文章,随后我会回来用别的点子给他交稿。然而,我后来还是吧啦吧啦地说起了布拉德利。
我在他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不管已经说过些什么,我们都会有兴趣。但他告诉我,当然不敢有任何保证。我写好故事,并寄了出去。
随即,莱奥·霍菲勒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打算买下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你以后再也不要找我说话了。从现在起,你就去找肖恩先生说,你要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忘掉我跟你说的那些事情,全都忘掉。保持一块白板。接着,他就带着我绕了个八英尺的弯子,然后就是,嗨,你好,麦克菲先生!我跟肖恩的交道就这样开始了。
《巴黎评论》: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
麦克菲:他说话很柔和。我对他肃然起敬:这个家伙就是《纽约客》的主编,他就是那个神秘人物。在我的写作经历中,跟他见面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努力上一百年的时间去了解他,而那才是第一天。不过,他的确是个很能鼓舞人心的编辑。肖恩一直担任新作家的编辑,所以他对那篇有关布拉德利的报道进行了编辑。我于是在他的办公室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标点符号。他不管解释什么都很耐心,整整看完了我那一万七千字,标点符号逐个逐个地过,从一个语法家和读者校读的角度引经据典。类似的细节,他跟作者逐一详谈,每个必谈。每次都是长谈。我曾经问他,肖恩先生,你要维持整个杂志社的运作,这个周末就要印出一期杂志,而你又是它的主编,现在你却坐在这里跟我讨论这些逗号分号——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回答说,该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这句话很中听,就写作而言,它莫不如此。该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
《巴黎评论》:比尔 · 布拉德利那篇报道发表后,他们给你工作了吗?
麦克菲:最后一稿送交印刷后,我在离开之前告诉他,我想成为《纽约客》的专职人员。哦!调子变了。肖恩从那个出色而仁慈的词句编辑变成了苛刻的顾客。他说,嗯,他怎么能鼓励这样的做法呢?我怀着强烈的热情才写出了这么一篇好的作品,而他怎么知道这不是一锤定终身呢?再说,我有四个孩子。他怎么能鼓励我放弃这份有薪水有福利的工作呢?他说,我在道义上不能这么做。他这是在把对话引向真正的死胡同。
我说,有了这次经历——发表了一万七千多字,还带着一个作家的满足劲儿——我又怎么能回到《时代周刊》继续写短篇报道呢?我还说,如果我不能在这里全职写作,我就打算去一家银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工作,同时试着以独立身份给《纽约客》写稿件。
肖恩的答复是,好好好,我明白。好吧,你就加入我们吧。就这么定了。我就走出了办公室。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年初,也是我成为专职作家的时刻。
《巴黎评论》:你做完调查之后,如何进行写作?
麦克菲:我首先是抄录笔记。这可不是纯粹的机械过程。一边摘抄笔记,一边就有各种想法。你对于结构就有了主意。你对选词,也就是措辞也有了主意。我在打字的过程中,如果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会在脑子里把它快速地捋一下。等我抄录完毕,某些想法也就形成,并得到了累加,就像一块磁铁吸到了铁屑。
如此一来,你在桌子上就有了一堆的材料,这跟小说作家有所不同。小说作家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他们是靠感觉来写作,靠感觉呀——更多的是一种试错并带有探索性质的东西。就非虚构而言,你找好了材料之后,需要努力做到的事情就是把它像讲一个不违背事实的故事那样说出来,而与此同时,它的结构和呈现方式要使之读起来富有趣味。
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讲,做饭的过程与之类似。你进到商店,买了很多东西,把它们拿回家,摆上厨房案板之后,你就要用它们做出一顿饭来。如果其中有一只红辣椒——那它就不是番茄。你就要用你所拥有的东西来进行加工。你不可能在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收集到理想的素材。
《巴黎评论》:接着呢?
麦克菲:写开头部分呀。我于是坐下来并开始思考,我该让这篇文章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如何写才有意义?不能把它写得俗里俗气。它得符合你的预期。它应该像一支手电筒,照亮全篇文章。于是,你就写起开头部分来。接着,你又去翻阅笔记,开始寻找关于总体结构的思路。你如果写好了这样的开头部分,整个过程将变得简单许多。
我写好开头部分后,会阅读笔记,并反复地阅读,直至滚瓜烂熟。思路已经有了,但我一贯的做法是寻找合适的法子,对素材进行细分。我要寻找那些能够形成衔接,并具有关联的素材。我给每个片段都进行了编码,跟机场代码有些类似。比如,某个片段跟纽约州北部有关,我就在边上写上“UNY”字样。完成所有片段的编码后,数量庞大的笔记就变成了一则则带有编码的短小记录。然后,我会把每个编码都写到一张索引卡片上。
《巴黎评论》:你在各个片段之间是如何过渡的?
麦克菲:你得寻找合适的并置关系。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并置关系,你就无需操心那些在我看来属于白痴的东西,比如平稳过渡。如果你的结构真正地通顺合理,你可以写得有所跳跃,而读者也会紧紧地跟着你阅读下去。你完全无需在这两个部分之间架桥搭绳。
《巴黎评论》:这个方法是如何得来的?
麦克菲:它可以追溯到普林斯顿高中时期的奥利弗 ·麦基,以及我们在进行任意类型的写作之前必须完成的结构大纲上。这个东西我在《时代周刊》工作时再次用过。我的第一篇封面报道就卡壳了。文章有五千字,那一大堆材料让我大费周章。我感到十分沮丧。材料很乱,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纸片,我不知道需要的东西在哪里。于是,我就想起奥利弗 ·麦基和大纲来,在一大摞材料里进行筛选,把它们划分成一个个片段,并逐个进行处理。
《巴黎评论》:有没有变得过于机械的可能?
麦克菲:听上去很机械,但效果正好相反。其作用就是让你获得解放,可以自由地写作。你的笔记全都摆在那里,你一大早就投入写作,通读一下自己想要写的内容,而需要阅读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部分,因为它们都在别处的文件夹里。只有你和手下的键盘。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你让自己摆脱了机械性。写作、措辞、情节都会手到擒来——前提是你先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边。你可以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浏览那些彼此关联的笔记,你也就知道,这些就是你希望涵盖的内容。而到了这时,你就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等着信手拈来。
听起来可能是我拥有某种用于写作的公式。没有,绝对没有!这完全要靠你自己——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好吧,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写作。但我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写下第一个字。我要泡茶。我的意思是,我曾经会拿出一整天的时间泡茶喝。还有体育锻炼,我隔天做一次。在原来需要削铅笔的时候,我还会削铅笔。我把铅笔削完就行。10点、11点、12点、1点、2点、3点、4点——每天如此。差不多每天如此吧。4点30分,我开始着急了。这就跟弹簧差不多。我感到很不开心。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一直这样子,那么这一天就算是废了。5点:我开始写作。 7点:我就回家了。这样的情形一次次地反复发生。那么,我干吗不去银行工作,然后在 5点钟进入这种状态并开始写作呢?因为我需要瞎晃悠的那七个小时。我只是没有那么自律。我上午没有写作——只是在试着写作。
《巴黎评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都在写作,而当时多在讨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你当时对此有何态度?你是否感觉到非虚构写作领域具有了某些不一样的东西?
麦克菲: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周日杂志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通常被称作某种革命,但我一直没能弄得太明白。非虚构写作并不是从一九六〇年才开始。往前可以追溯那么多的非虚构类作家,比如利布林?瓦尔特 · 洛德(Walter Lord)、詹姆斯 · 艾吉(James Agee)、阿尔瓦 · 约翰斯顿(Alva Johnston)、约瑟夫 · 米切尔(Joseph Mitchell )——这些都是非虚构文学的开拓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写过很多比所谓的新新闻主义要优秀得多的作品。不过,亨利 · 大卫 ·梭罗仍然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闻主义作家,一如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为《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写作的多萝西 · 戴伊(Dorothy Day)、艾达 · 塔贝尔(Ida Tarbell)、薇拉 · 凯瑟,还有约翰 · 劳埃德 · 斯蒂芬(John Lloyd Stephens)、小理查德 · 亨利 · 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 ),以及更早的托马斯 · 布朗、罗伯特 ·伯顿、弗朗西斯 · 培根、詹姆斯 ·鲍斯韦尔和丹尼尔 ·笛福。你说得很对。
新新闻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为了贴标签而贴上的标签。部分作品读起来的确很有趣,但这个“新”字面临很多先例的挑战。每当有人称我为新新闻主义者时,我都会尴尬地眉头紧蹙。
汤姆 · 沃尔夫帮忙让这种写作类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他只是汤姆 · 沃尔夫。非虚构写作的形成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在这么做,而是因为长时间内有一大帮人有兴趣根据纪实性材料进行写作并以此立足。他们可不只是简单地写几篇文章,告诉你如何摆脱低温症。
《巴黎评论》:就兴趣而言,或就人们看待非虚构写作的态度而言,有什么重大变化吗?
麦克菲:整体而言,唯一的重大变化是人们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件比用于裹鱼烹饪的东西更重要的事情。它赢得了各种形式的尊重。我读大学期间,没有老师讲授我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写作类型。该话题不在学术机构的讨论范畴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我收到前往犹他大学做读书活动的邀请。我接受了。几个星期后,与我联系的人回复我说,他感到十分尴尬并深感抱歉。尽管他希望我前去犹他大学举办读书活动,并与学生展开交谈,但他的同事们并非如此。他们不认可我写作的这个体裁。我复函说,我对他希望我前去出席活动一事真的深表感谢。对他我肯定感激不尽,可对他那些同事——等他们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会站在灯下看着手表。
《巴黎评论》:你把你自己所从事的写作类型叫作什么?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有时候叫作“纪实文学”(The Literature of Fact),有时候又叫“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 )。
麦克菲:我更愿意称之为纪实性写作(factual writing)。别的名称都有瑕疵。不过,“fiction”(虚构/小说) 这个词一样有瑕疵,这个名字用起来很古怪。它不指代任何事物,而只是意味着“被创造”或“创造”。它的词源是facere。实际上,我们不能给某个东西加个括号,然后说这就是那个东西。有的小说家写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很垃圾、很恐怖;也有人写得很好,并以此改变了世界。这就是 fiction。好吧,它就是个名字,意思是“创造”。因为你没法用一个单词来定义它,那干吗不用类似的简单词语呢?
至于“nonfiction”(非虚构/非小说)这个词——老天,那相当于在说,我们今天吃了一顿非葡萄水果的早餐。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你吃了一顿非葡萄水果的早餐。想想吧,你对这顿早餐的了解有多少。我不反对这样的东西,因为挑选过程很艰难——就跟给孩子起名差不多吧。你要知道,名字这个标签会伴随孩子一辈子。
《巴黎评论》:回忆录也已经变得很流行,但你对你自己写得很少,为什么呢?
麦克菲:我从来没有兴趣描写我自己,或者说(谁都知道),把我横插在读者和阅读材料中间。不过,如果作者适合或者需要出现在文章中,那么他就应该出现在其中。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某处登上了一艘橡皮艇,而他后来写的是,一个访客登上了橡皮艇。好吧,就这么写吧。如果非得如此,那你就得出现在文章中。
举个例子,《三角形南瓜籽》(The Deltoid Pumpkin Seed)是一个有关无数次飞行试验的故事,其中就没必要宣示我的存在。我显然出现在了现场,要听要记,但不用提到我。随即,我写好了六万字的稿子,而快要到结尾的时候,也就是高潮所在的部分,飞机终于飞起来了。一个名叫爱福莱特 · 林肯霍克(Everett Linkenhoker)的家伙跳上一架派珀切诺基飞机,准备驾着它试飞一圈,我跳上去坐在了他的边上!我们起飞了。在我要提交的稿子中,该写谁坐进了飞机?访客吗?所以我写的是:“我跟着他坐了进去。”我提交了一篇六万字的文章,其中仅这一处用到了“我”字。这让我在《纽约客》的编辑罗伯特 ·宾汉姆无法忍受。他感到很不安,这让他无法面对仅有的这个代词。他说,仅此一处啊。我回答说,鲍比,你看,文章中只有这个地方适合用上一个代词。他说,你得再加一个。我说,你看,其他地方都没有必要用到代词。他又说,你一定要再加一个;这样可不行,你不能在全文只用这么一次。我回答说,好吧。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幅场景,有一个加油站,好像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内沙米尼(Neshaminy)吧,修车铺的一个机械师正在捣鼓什么东西。我就想着,好吧,我可以写成我看见那个机械师正在干活。就这样,我在这里,可能还有另一个地方加进了一个“我”字,宾汉姆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开始从事教学的?
麦克菲:一九七四年圣诞节到元旦那个星期,我接到了大学打来的电话。他们之前连续四个学期聘请《春城花满天》(The Best LittleWhorehouse in Texas)的共同作者拉里 ·L. 金(Larry L. King)担任教学任务。你如果连续四个学期聘请一个四十多岁的记者从事教学,那他就很难继续维持记者身份。拉里 ·金在圣诞节期间挣扎过、爆发过,什么事情都干过,并最终一辞了之。我当时正好隔街而居,他们于是打电话问我,你要不要干?我说可以。是马上哦,根本没有我通常那种做法——哦,好的,我得想想,能给我一周的时间吗?要是放在几年之前,我可不会这么做。当时是一九七四年年底,我从一九六五年起就在《纽约客》全职写作了。这是事后回想,但一篇接一篇毫不间断写完之后,能有个间歇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我有个好友在迪尔菲尔德学院教英语,他告诉我说,别这么干。他说,老师一大把,作家很少见。但我现在的看法是,自我从事教学以来,我当作家的创造力要胜过不从事教学。在整体轮作框架下,这是一份相辅相成的工作:我要看别人的写作,而压力就不是要我自己去写。不过,我看完之后的感觉很新奇。我的工作安排是在三十六个月里从事六个月的教学,老天,这让我有一大把的时间从事写作,对吧?
《巴黎评论》:除了让你获得休整,教学还对你的写作有别的作用吗?
麦克菲:我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会一直就这么教下来。我没想到自己从教的时间会超过三个月。不过,我同样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跟那么多教过的学生保持联系。这就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就在去年,我的班上头一次出现了一个学生,他的父亲也当过我的学生。
然而,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的学生有所互动——是一件令人为之一振的事情。我已经七十多岁,而我教的这些孩子确实让我充满了活力。一个人十九岁就成了真正的好作家,并且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写作这个话题,能跟这样的人交谈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我不想停下来的原因。
不过,我确实写得够多了。你不应该写得过多。我跟你实话实说。
《巴黎评论》:此话怎讲?
麦克菲:我认为有的人不应该写很多书。我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追求。或者说,我觉得这么多书加起来也不一定算得了什么,尽管我非常崇拜洛佩 · 德 · 维加。他一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据说写了一千五百多个剧本。
《巴黎评论》:根据多年的教学来看,你很明显地相信,关于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事项是可以教会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无法教会的东西?
麦克菲:重要的一点是,写作要靠写来教。人们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而他们也会表明类似的观点,即写作无法教会。这个问题是,对的,你不可能朝地上扔一个鞭炮,然后就炸起来一个作家。但写作可以教会,类似于游泳可以教会。我在凯威丁夏令营当游泳教练期间,所教的孩子都学会了游泳。每个孩子都会游泳。然而,当他们在水里游动的时候,效果各不相同。你可以跟他们讲解呼吸、节奏,以及手臂和胳膊方面的问题。
写作老师也能这么做——只要他的脑子里时常装着作家各有千秋这一点。你如果试图教会他人按照你的路子去写作,那么这似乎就是一种徒劳之举。你只需要对他们的作品加以评价即可,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净效用的问题。
《巴黎评论》:我觉得,年轻作家面临的难题之一,是明白写作没有明确的路径。
麦克菲:没有路径。你如果上的是牙科学校,毕业之后你会当上牙医。对年轻作家而言,就好比看到了河流中的小岛,而你所拥有的就是这么一点东西——那么,你要何去何从?一动手就写大部头,这可能就是个错误;这会让你不停打转,显得自己无能。比如说,二十一岁是犯错误的好时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岁呢,每长大一岁,犯错误的代价就增大一点。等你到了四十五岁,就别指望还要犯这样的错误。不过,重点是,在你驾着船绕过这些小岛的过程中,在你寻找水流绕过它们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都有其价值。
《巴黎评论》:你是否担心作家的出路正在不断减少?
麦克菲:我确实有些担心。没有人知道它会发展到哪一步——尤其是就互联网和纸媒的关系而言。然而,写作不会消失。会有一个重大调整——大家能想到的是,它类似于篮球或长曲棍球比赛中的球权转换,整个局面陷入不稳定状态。不过,在不稳定的区域仍然存在大量机会。我们有了互联网,就处在了类似的区域。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很难想象写作本身会消失殆尽。那么,好吧,它将如何发展?它是一股流体力量:它会通过缝隙冒出来,它会绕着角落流动,它会从屋顶涌出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我就该像现在这样给大家提出忠告,也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作家,你应该考虑写书。我认为,书不会消失。
《巴黎评论》:就你自己的写作项目而言,你说你觉得自己会少做一些偏重于报道的项目。为何如此?
麦克菲:哦,或许仅仅是因为精力吧——也就是要离家外出,在某个地方的汽车旅馆睡觉,并停留一两个星期。问题是,我想找到写作的题材,所以这让我觉得它是一件麻烦事。我上次离家外出,并就某样东西写了一篇报道,那是四年前的事情。我如果现在离家外出,前往安肯帕格里高原做点什么事情,并独自待上三四个星期——我现在的动力就没那么强大。
《巴黎评论》:但是,写作本身并没有变得更容易吧?
麦克菲:没有。只有写出第一稿后,你才会变得成熟,并获得经验。接着,在我身上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感觉轻松了很多,而不再有琼 ·狄迪恩所说的那种“低恐”(low dread)感觉——这个词用得太好了。狄迪恩谈到她坐在起居室里,看着书房的房门——仅仅是看着那扇门,就让她产生了“低恐”感。在当作家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会如此。
我的写作方法有所改变。我原来就是不停地写呀写。我不会因为已经克服了所有的恐惧而停下写作。我会一直写到深夜,甚至写到凌晨两三点。然而,我逐渐明白,这么做非常低效,因为等我下次再能提笔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两天半或更长时间之后的事情。如果写到七点停笔,那么到了月末,你会写出更多东西来。于是,我就在七点停笔了。如果一个句子写了一半,而我又兴致盎然,并且进展顺利,到了七点我同样会起身回家。
《巴黎评论》:所以,这个规律很严格。
麦克菲:规律出效益。然而,每一天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让自己有所改变和调整;你必须经历某种改变,从一个正常人变身为某种类型的奴隶。
我根本不想刺破这层膜。我会尽可能地避开它。你得进入里面,而你不想进入里面,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压力和负担,你也只想留在外面,成为你自己。因此,进入那种状态的那天就是一种不断的挣扎。
如果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高产作家——这听起来会很奇怪。这就像地质时间和人类时间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确看似写了很多东西。但是,那是我每天坐在那里,一坐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动手下笔的结果。一周六天都遵循这样的作息,才能让桶里每天都增加一滴水,而三百六十五天之后,桶里才会多少有一点水。
购书↓
稿件初审:骆玉龙
稿件复审:董彦乐
稿件终审:刘 燏
相关知识
何伟为《巴黎评论》采访他老师约翰·麦克菲的这篇访谈终于出版了
《巴黎评论》专访余华,中国作家首登老牌栏目“作家访谈”
书讯 |《巴黎评论·出版人访谈》:为您讲述文学出版的奥秘
余华成为《巴黎评论》史上首位受访的中国籍作家,访谈内容收录《巴黎评论》杂志2023年冬季刊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研讨会:他山之石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余华成为《巴黎评论》史上第一位受访中国作家
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作家约翰·巴思去世,享年93岁
潘凯雄、来颖燕、行超聊文学访谈:采访是一种“双向奔赴”
刘亦菲接受嘉人采访花木兰娱乐评论大赏
伊恩·麦克尤恩将出版新书:一部“没有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3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71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7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9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34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