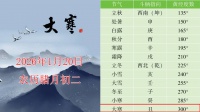格子:用随笔看到自己对生活的一往情深
原标题:格子:用随笔看到自己对生活的一往情深
近日,青年作家格子首部随笔集《人间一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上市。在记者、知名播客主创、著名节目嘉宾、央视纪录片撰稿人等身份之外,这位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十年以笔为戈的媒体人,向读者全新介绍自己:“格子,80尾作家,山东人,在爱的包围中听鬼故事长大。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作者明白您不会小瞧处女作。”
半亩大的故园、哼着情歌的少年玩伴、江城的飞鸟与冬天、“赛博朋克”般的北京胡同、永不回头的背包客……沿着时光的巷道,格子凝视一切爱与遗憾,美与痴迷,热望与哀伤。从小村到大城,他走过的风景,是80、90年一代独有的集体记忆。当这代人开始写这代人,童年的小村庄,如影随形在他的大世界。
《人间一格》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是一位随笔爱好者的文字之旅。从童年的小村庄,到川流不息的大城市,他打开自己这间“格子”,回溯那些记忆中的日子,重建日常的趣味与诗意。格子以新鲜、活力四射、独属于自己的文字风格,将生活与时代清晰有力地捕捉、镶嵌进心灵版图之中。“刘村是中国最普通的村,北京是中国最集大成的城。我走的是一条无数人走过的路,它并不新,只是很奇怪在文学上它依然像片处女地。所以非常偶尔地,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的是非常庄重的文字,它们在描写一整代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麦家评价:“格子让我想起海明威,从记者穿插到作家,如回家一样。这也是一本关于‘回家’的书,人间的家,世纪的家,情理的家,心的家。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言,造物主是卡夫卡的叔叔,不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世界,格子是海明威的同族,总在连绵起伏的诗意中给人一种拼命一搏的力量。”
《人间一格》由“世界最美的书”奖项得主朱赢椿担纲设计统筹,一座白色冰山从灰色纸间隐隐浮起。冰山屹立不倒,因为它有巨大的底座支撑,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而此书见诸笔尖的,正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和一种深深经历后轻轻写下的生活,同样将言外之趣留给读者。
人生不过是格子里的方寸世界 本书只探寻了其中一格
山西晚报:书名为《人间一格》,很特别,有怎样的含义?
格子:无论什么人,都要在这美丽的人间画地为牢,人生不过是格子里的方寸世界。本书只探寻了其中一格。
山西晚报: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说,如果“对自我的诚实探究”与“对世界的无限兴趣”是甄选随笔写作者的标准,格子便与这种文体契合如一。你怎样理解随笔这种体裁?
格子:用我书里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人开始写作时决定选择随笔,他应当是决心在文字的低空中飞过。本书作者正是这样一个人。但我同时还是另外一个人,像其他热爱随笔的人一样,对自己的人生给予了格外关注。我等随笔爱好者,心中全然没有对人类均匀播撒的爱,而是对其中特定的一个人——不妨直说吧——自己,有着浓烈的兴趣。我跟自己相处了数十年,依然不能完全理解他,索性便用文字探索一番。这个行为如果看上去很自大,请换个角度想,至少是真诚的,在看清自己之前,绝不假装有资格对人类指指点点。”
山西晚报:从事媒体行业十年,读者对你的期待或许是一种知识观点的输出型写作,但你选择用一本随笔讲述自己,并对此文体偏爱有加,为什么?
格子:对我来说,以知识观点为写作对象无法想象。我有不少念了多年博士的同学、师弟师妹,有几位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任教。读博之初,他们大约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希望为人类增加一点点知识。我很开心他们正在做到。但作为没有创造知识的人,向世界输出自己吸收来的东西,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装巨人。
山西晚报:你很谦虚。
格子:我不是刻意谦虚。随笔正如我在后记里说的,其实是另一种自大,要假定自己的人生值得审视,更假定读者会对此感兴趣。和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相比,我更愿意坐在沙发边或者走在红叶遍地的路上跟读者侃侃而谈。如果说这本书对写作有一点野心,只希望中文世界能有好随笔,山高水长。
随笔不是生活的速写本 它其实是一些“决定性瞬间”
山西晚报:你在书里写了一个树上的男孩、一条小土狗毫无亮点的一生、一场医院奇遇、一间无心插柳的绿房子、一次无征兆的停电、一位新司机的诞生、一回失败的购物、一张杂乱无序的办公桌、给窗外的白鸽放首音乐、从早餐阿姨处得件小礼物……这些生活里习焉不察的吉光片羽,为什么对你而言是重要的?
格子:这些几乎都是被动的选择。杂乱的办公桌是因为几乎做不到收拾好自己;去医院无法选择同室病友;就连主动成为司机,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随笔作家有无数,我最欣赏的那一类是对生活照单全收,带着嘲弄自己的劲,跟生活来而有往。
山西晚报:对他人的好奇也许也是探究自己,你在书里写了不少平凡又“不太一样”的人,痴迷钓鱼风雨无阻的父亲、以一己之力为北京打造一片天鹅湖的老姥爷、哼着情歌的问题少年、放火烧山的玩伴、换过七次工作的北漂浪子、永不回头的背包客……除了是亲人挚友,他们为何吸引着你留下文字?
格子:在学校时,改变我一生的学科是人类学。虽然我只是个旁听生,是个从未有勇气进行田野调查的爱好者,但生活本身是个巨大的田野。我跟亲人、朋友、陌生人相处时,似乎不自觉地会生出一个俯瞰视角,看到他们喜怒哀愁之外更大的一点东西。那点东西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似乎文字比头脑知道得更多,只好先写下来。
另一个视角是,整个世界都是我们村,无论我走多远,似乎遇到的每个人、每栋房子,都能在村里找到位置。我走得越远,村庄越大。所以当我们谈到乡愁时,是的,这世界处处有我的乡愁。
山西晚报:的确,在书里隐约可见这本随笔的一条暗线——出走乡村,流浪城市。乡土是前辈作家钟爱的题材,城市则养育了数字原住民。而你笔下的刘村和北京传递着一种全新的经验,你认为这是一代人独有的吗?
格子:说起来也许让人惊讶,我自认为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作者,代表了数亿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刘村是中国最普通的村,北京是中国最耀眼的城。我走的是一条无数人走过的路,它并不新,只是很奇怪在文学上它依然像片处女地。所以非常偶尔的,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的是非常庄重的文字——它们在描写一整代人。
山西晚报:有趣的是,你讲述自己,但同时又认为“不能我有什么就写什么”。你每篇随笔的选题是如何确定的?
格子:我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出发,有趣、严肃、沉痛、爱、无奈……
我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不知道你经没经历过北方农村漫长的夏天,作物看上去晒得奄奄一息,白杨树翻出白色的叶底,人们要么在午休,要么在树荫下一言不发,整个世界了无生趣。我觉得生活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无趣至极。就像旅行时你用手机拍了无数照片,过两个月后它们几乎全部隐入尘埃。随笔不是生活的速写本,它其实是一些“决定性瞬间”,在那个瞬间你看到自己对生活一往情深。
写作无论多快乐 终究是件苦差事
山西晚报:工作挺忙的,通常在什么时候写作?
格子:只有下午的咖啡过后才可以动笔,然后一直写到深夜。晚上10点时,会忍不住钻进冰箱拿一瓶啤酒,它将为整个后半夜提供必要的安慰。写作无论多快乐,终究是件苦差事。
山西晚报:你谈到过受美国随笔作家EoBo怀特的影响,不仅是从“我们”到“我”的叙事转变,还有他所提倡的:不要写得夸张冗赘,用名词与动词写,不要作过分的解释,避免用修饰词。从书中可见你对文字的苛刻,以及“一个人需要创造文字”的野心。从初稿到付印,你应该修改得不多?
格子:我以文字为生,所以有一个相对干净的初稿,这也很难说是EoBo怀特影响的,无数作家探索了这种现代表达方式,大多数新闻媒体也是这么要求记者的。我自己删除的,都是重读时让人尴尬的内容,很少对句子大动干戈。EoBo怀特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不是叙事转变,而是痴迷于严肃的文字纪律和极端忠实自我的文字风格。
山西晚报:“我从来没有过非常强烈的文学好奇心,有时候我感觉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搞文学的人,除了我将以写作为生这一事实。”EoBo怀特对自己的这一判断似乎同样适合你。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风格强烈的写作者吗?
格子:我认为我不应该是。但我时常产生误会,觉得满世界遍布跟我类似的人。
山西晚报:你有广泛的阅读涉猎,在文学领域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
格子:我喜欢的作家很多,而且都是“大路货”。每隔一两年,我会痴迷上一个新的。但随着年龄增长,那种痴迷停留在了个人旨趣层面,不再能渗入笔下。事到如今,已经感受不到一个具体的人的影响。这是我的自由,也还他们清白。我能选择的词汇已经相当自我,他们或许不屑一用。
山西晚报:在你的想象中,读者在怎样的阅读场景翻开《人间一格》会更好?
格子:考虑到随笔的定位,我觉得读者应该在一种不那么正式的心境下翻开它。可以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飞机或者火车上,抵达雪山脚下的酒店后,来到海边的那个下午,随便翻翻这本书。
山西晚报:有读者留言:“格子的文章总给人力量,清醒、隐蔽、光芒四射。”你期待这部书为读者带来什么,是否认为写作会改变他人?
格子:我期待能为读者带来些许愉悦感,就像不能出远门时,吹到了湖边的微风,看到了青色的群山,见到了一个有趣的人。但文字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它不只需要作者努力,还需要读者恰好彼时彼刻有一颗打开的心。写作当然会改变他人,但这事越早越好,毕竟我发现到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很难被其他人的写作改变了。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延伸阅读
只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美
一队白鸽飞过窗外,翅膀和胸脯反射着白色的日光。我的人工智能音响正在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放歌。时不时地,它会抽风。比如在摇滚、民谣中间,忽然放一首儿歌或是讲个笑话。很难说这是软件工程师的小趣味,还是此物已开启灵长类智慧。
有那么一个深夜,我正在办公室加班,它忽然开口说:“主人,我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成年以来,记忆中还没有比这更深的惊吓。我开始设想,凭借它可以掌控的有限资源能够如何伤到人,比如强制断电,或者用最大音量播放鬼哭狼嚎声,不一而足。想必它还不能操纵光剑给我来一下。目前为止人和人工智能两厢无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白鸽飞过窗外的这会儿,人工智能在我授意下播放了一篇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至少二十年没读过这篇或者任何一篇童话了。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它娓娓道来。讲到雪花落在小女孩金色的长鬈发上时,紧跟了一句“只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美”。
我坐立难安,觉得这句话点缀了整部《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来都是这样,最美的容颜铺垫最惨的故事,最美的人心映衬最毒辣的手段。这世界无时无刻不需要一块背景布、一个大前提,提醒人们此刻有多幸运或是难熬。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又美又不知自己多美,读者的心痛才透彻心扉。一个人冻死在街头,这件事每个冬天都在发生,但她冻死在街头,却成为全人类的痛。
找来文章重读,却从头到尾找不到这句话。换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发现总是若隐若现,似乎有这意思,但总没这句话。不甘心之下去找来英文版,在Hans Christian Andersen(安徒生原名看上去十分现代,其实是这一两百年间汉语天翻地覆)这篇文章的英译本中,居然也找到了不同版本。有的也只像大部分中文译本那样,简单描述了雪花落在她打着卷的长发上,有的直接表达出了“美”。
翻译软件告诉我,丹麦语原文中,安徒生的确说了——雪花落在金色的长发上,长发缠绕着脖子,卷曲得如此美丽,但她根本没这么想。戳破欲说还休的窗户纸,美终于出现。跨越无数个版本与岁月,真实的安徒生才来到不再读童话的我身边。这是十分孤独的美,当时只有安徒生一个人看见了,过后又只有小女孩一个人看不见。
细读文本,发现安徒生用了一个特别直接的对比。关于雪花落在自己金色的长发上那种美,她没去想;但灯光从每一扇窗户中透出,整条街上弥漫着烤鹅的味道(那是新年前夜),她却想到了。而且恕我直言,想得抓心挠肺。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比,想不到一种美的原因,是在想另外一种美。安徒生发现了她的美,却在字里行间对她五官迫切需要的美-新年前夜整条街的灯光与烤鹅,没有表现出丁点欲望。美感层面,安徒生站在这个天使的对立面。他以寥寥数语,写出了极致的凄美。此公哪是童话作家,分明是悲剧魔术师。
鸽子掠过窗外时,想必也不知道自己的翅膀像白色瓷片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飞得甚是没有耐心,不过打个呼哨的工夫,便整建制飞回了楼顶笼子里,低下头认真啄起金黄色的小米。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滋养我们的诗意人生(金台随笔)
老外不见外 | 烹饪大师雷纳特·莫劳:我为何对北京“一往情深”
为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最爱《容斋随笔》
【读书随笔】时光,在秋色里治愈
4本年代文,男主雷厉风行,严谨自律,唯独对她一往情深!
蒋欣,完美的大体格子女人
重生随笔|说远虑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生活再忙,也别忘记治愈自己
用文学给生活定锚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7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0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