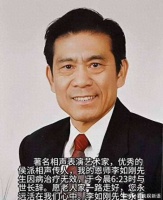茶苦唯自知——读《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原标题:茶苦唯自知——读《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作者 | 莫雨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周作人晚年,应曹聚仁之约,从1960年12月起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回忆录《药堂谈往》,1962年11月完稿后更名为《知堂回想录》。1974年4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1995年初,在周作人之子周丰一及其家人的支持下,敦煌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大陆版,定名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苦茶之名,或源自周作人著名的《五十自寿诗》之“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句。《五十自寿诗》本名《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初仅一首,是周作人一九三四年初所作的“打油诗”,后用原韵续作一首,一起发表于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时,林语堂给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此后,这两首诗便以《五十自寿诗》驰名。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书末的版权页标注:“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2 次印刷”,“印数:5001—25000”。此书3月1版1印,只印了5000本。1995年,吃螃蟹的敦煌文艺出版社也颇惴惴:周作人的书不知有人愿买有人想读否?所以先印5000本试水。这一试,虽未掀起什么洪涛巨浪,至少是涟漪层泛,不绝如缕,扩散得很广很远。短短一月,初印的5000册就销售一空,于4月又加印了20000册。可见当时,愿买想读的,大有人在。我是愿买的人而且买了,是想读却一直未读的人。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突然有了兴致,从书柜深处搜出来读。
最早知道周作人,是因为鲁迅。鲁迅周树人如日中天的年代,虽讳言周作人,却约略知道鲁迅有两个弟弟:一个坏,叫周作人;一个好,名周建人。后来知道得多一点,知道周作人与鲁迅反目不相往来,知道周作人抗战时出任过伪职,而周作人的文字有不同于鲁迅的风格。再后来,虽想起周作人的人生经历总是不爽,却渐渐喜欢上了他的文字,觉得其中有一股子说不出的韵味,挑我读欲,动我心弦。他上接《世说新语》,中续明清小品文,后起废名、沈从文等,再延及汪曾祺、林斤澜等的文风、笔法,正好对上我渐行渐老的年龄和阅读口味。由此,周作人在我这里不再是别人的什么人,也不只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符号,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化人,就是他自己,就是周作人。
见到周作人的书都比较晚,买得多,读得少。上世纪八十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经推出过一套“百家散文书系”,陆续买了十多本,其中有《周作人散文选集》,翻过,印象最深的是《前门遇马队记》。1993年,文联出版公司曾经推出过一套“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名列其中,很认真地读过,觉得有味道,特别是《故乡的野菜》,值得咀之再三,嚼之不已。本世纪初,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书系,断断续续买过几十本,其中有周作人的《我的杂学》,读过,对周作人之“杂”,对其述“杂”时或许存在的那份“骄傲”,佩服不已。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钟叔河主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共14册,虽然标价很高,却依然买了回来,码在书柜里,随时翻查。2017年,买了钟叔河笺释的周作人做诗、丰子恺插图,海豚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杂事诗笺释》,一一读过,虽所记多是浙绍风情,但很是喜欢。2020年10月,岳麓书社再版钟叔河、鄢琨编订的《周作人作品集》,因想读周作人的自编集,又买了一套回来。
读《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最想了解三个方面的事情: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原因,周作人出任伪职后的经历,周作人新中国时段里的人生。但很遗憾,这三方面的事情,周作人都语焉不详。
关于兄弟失和。第一四一则“不想辩说(下)”有段话:
这回讲到一九二二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说的其实只是最末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直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就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文中的“那篇东西”,指周作人1940年5月所写的《辩解》。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一是周作人不会说与鲁迅失和的原因,二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一日与鲁迅正面冲突时,有徐耀辰、张凤举、许季茀(寿裳)在场,三是许季茀“造作谣言”,四是鲁迅生前未曾谈及失和之事。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许季茀“造作”的“谣言”: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原因是听了妻子的言说,而羽太信子所说又涉及到鲁迅和周作人都不愿提及的难言之隐。现在,当事三人都已仙去,原因究竟为何已无从查考。后来者,最好还是遵从当事人之意愿,不打听为好!
关于出任伪职用其后。第一七八则“从不说话到说话”里有几句:
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里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理。
周作人不写“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是周作人作文的自由,有没有羞惭的原因,不可妄加揣测。本来,不写就不写,没什么大惊小怪,但紧接着偏又用两则的篇幅,来写“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片冈铁兵在所谓“大东亚作家大会”上发表《扫荡反动作家》演说的这段公案,就令人觉得奇怪了。可见周作人讲“主张不辩解主义”时,虽或许是真心,但却不可全信。
关于建国后的人生。周作人以“我的工作”为名,用了六则的篇幅来谈建国后,谈的全是工作,内容多是翻译外国作品。对于自我的创作,很少谈到。对于生活,几乎一概不谈。以周作人的老辣见识、平和心态,建国后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是必然的。但周作人终究是周作人,他在夹着尾巴做人的同时,偶尔不经意的言说,却透出其平和外表下颇为高傲倔强的性格。比如第一九四则“拾遗(戊)”之“读小说”里有段话:
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得罪作者。
本来说到此即可结束,但周作人偏不,偏要用一个破折号,再说几句话:
——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藐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乱说,应该是批评,至少不会是一味的赞颂。“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藐视”,藐视之义,清楚明白,新文学在周作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这句话里的清高、骄倔,可不只是一点点,而是满满当当甚至已经溢出盆钵,与周作人冲淡的性情,大异其趣。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的文字虽偶有讥诮,总体上却波澜不惊、言简意赅。娓娓絮絮的三十多万文字里,有他八十多年的所见所闻、所历所遇、所书所作、所思所想,虽因时空阻隔渐至模糊,却可窥时代烟云,回望之余,令人怀想不已。《苦茶——周作人回想录》里的周作人虽偶露峥嵘,总体上却内敛谦抑、平淡冲和。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知道该说的能怎样说,应怎样说,他说时或寓深意,我读着多能体会,说读之间,仿佛早有默契。
写“回想录”时的周作人闭户杜交,枯坐寒斋,独饮苦茶。在咀嚼自己人生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些苦涩呢?茶苦,茶苦而后甘,茶甘,茶甘而回苦。苦茶品咂再三,其中滋味,唯他自知。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爱是一杯茶
自律是成功的标配,吃不了自律的苦,就得吃平庸的苦
任见:茶饮里的远东浮世风雅
四个小技巧,让你的茶好喝一百倍
谢其章︱一部《陶庵回想录》,半部上海文艺期刊史
【美文悦读】周作人:中秋的月亮
任辉:把南茶引种到东北
生活如水,人生似茶
茶逢知己千杯少,喝茶是一种小确幸
兄弟刚从泰国回来,这…《李茶的姑妈》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7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0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