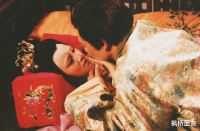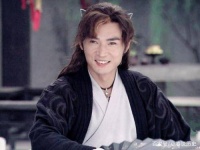这里的人永远在苦难里爬行,吐出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
原标题:这里的人永远在苦难里爬行,吐出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
点击上方图片直接购买《单读 32·寻找救生艇:爱尔兰文学特辑》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因此,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整个爱尔兰岛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写作,具体数字不详,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惊人地高。”
正如《单读 32·寻找救生艇:爱尔兰文学特辑》客座主编颜歌在序中所写,爱尔兰是一座文学浓度相当高的岛屿,除了乔伊斯、王尔德、叶芝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近年来也为一些中国读者熟知的奥康纳、希尼、托宾……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正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讲述此地、亦是属于所有人的故事。
颜歌希望这本爱尔兰文学特辑,可以向今天的中文读者介绍新颖的、多元的、受本地读者推崇的爱尔兰文学声音,以此遴选出了十二篇小说,分为三组,并一一向作者发出邀请。在这篇序中,她会为读者朋友们做一次导读,讲述曾旅居爱尔兰的她与爱尔兰文学产生的交集、她眼中爱尔兰文学的模样,以及选择这十二篇小说的原因。欢迎大家来到这方由小说家创造的故事里的世界。

故事里的世界
撰文:颜歌
去年年底,《单读》和彭伦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客座主编一期爱尔兰文学特辑。我即刻为这个提议兴奋不已,但又马上感到十分焦虑。我说我并不是短篇小说的评论专家,无法统筹全局,高屋建瓴,仅能根据个人口味做出选择,还有,这一辑能选多少篇小说?三十篇可以吗?五十篇?
就算能选五十篇,面对灿若星辰的爱尔兰当代文学界、那些组成了“爱尔兰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小说家们,我就像个只拿了一只口袋的大盗,站在堆积成巨山的宝物前面, 瞠目结舌,不知道该把哪个往袋子里放。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我是在 2015 年搬到了都柏林以后开始广读爱尔兰小说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我写小说写了二十多年,读小说的时间就更久,因此,比起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似乎和我的关系更近——如果我无法从文学里进入爱尔兰,那现实的爱尔兰对我来说 就是虚无缥缈、远若幻境的。只有拿起书,读了《死者》(“The Dead”),才觉得阿伦码头(Arran Quay)边上不再只有荒秃秃的红房子,反而充满了小圣诞夜车马往来的宾客欢笑;读了《基拉里峡湾》(“Fjord of Killary”),才发现梅奥郡(County Mayo)酒吧里酒鬼的呓语不再晦涩难解,倒成了末世荒诞的长短句;读了《欢迎光临》(“Show Them a Good Time”),才会在每次开长途车路过马林加(Mullingar)时不再抱怨寡淡的风景和索然的服务站,而是去仔细看这空旷的大地和在这份空洞里寻找意义的人们——对我来说,只有通过爱尔兰的小说,现实的爱尔兰才变得具体而意味深长,现实中人的话语才音律飞扬。这片土地被剥削和压迫了多年,这里的人永远都在苦难里爬行,永远在忏悔自己的罪,祈求无法降临的救赎;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向外敞开着自己,去感受,去表达,滔滔不绝,醉话连篇,诅咒,歌唱,吐出来最是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因此,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整个爱尔兰岛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写作,具体数字不详,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惊人地高。
刚刚过去的七月,在西科克文学节(West Cork Literary Festival)上,我在本地酒吧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刺人虻》( The Stinging Fly )新主编的莉萨·麦金纳尼( Lisa Mclnerney)。她跟我讲起她来之前终于看完了夏季刊的征稿。这次征稿特别面向之前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文学新人。“我本来以为不会有多少稿子,”莉萨跟我说,“你猜猜我们收到多少份短篇小说?”
我摇摇头。“一千两百多份。”她说。
而她需要从这一千两百多份投稿中选出十四篇来发表。
“不可能的任务。”莉萨叹口气,嘬一口啤酒。

《刺人虻》最新一期封面
***
这一次给《单读》编爱尔兰文学特辑的任务,虽然不如莉萨的任务那样不可能,但也谈不上轻而易举。我的想法是选一些新的、之前没有在中文世界被介绍过,或者相关信息还很少的作家和作品;此外,比起那些因为强化爱尔兰的刻板印象而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的作品,我更愿意选一些在本地的文学读者里受到推崇的作品——但这样的选择思路也可能会带来一个难题。
“很多爱尔兰作家尤其喜欢用本地话、土语,甚至自己造些新词,所以我感觉翻译起来可能会很有难度,我是应该选一些好翻的,还是就选我喜欢的?”我问彭伦。
“就选你觉得好的,翻译的问题我们来解决。”彭伦说。
▼
《单读 32·寻找救生艇:爱尔兰特辑》
现货发售中
得到了这样的保证,我第一个就把凯文·巴里(Kevin Barry)的小说放上了我的单子。凯文·巴里是爱尔兰最具 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他充满了方言、俗语、粗话的文学表达深深影响了现在爱尔兰的青年写作者,也是西爱尔兰作家群体中的核心人物。
一直以来,我总是偏爱西爱尔兰的作家。他们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凄风苦雨的斯莱戈(Sligo)、梅奥、戈尔韦(Galway),故事里的人讲话总是带着浓烈的口音,有挣扎,有绝望,有暴力,总是一片似乎要摧毁一切的黑暗,而这黑暗里仅有一丝若有若无却引人入胜的光亮。凯文·巴里是这样的,莉萨·麦金纳尼是这样的,科林·巴 雷特(Colin Barrett)和约恩·麦克纳米(Eoin McNamee)的故事也被这奥克斯山脉(Ox Mountain)下的同一片土地所孕育。
古来是流放犯人的康诺特省(Connacht),树木都被大西洋的狂风吹得斜着长,这里的作家也用各自的天才手段呈现出一个个扭曲的、迷幻的、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面前,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站立和观看的方式来和它们保持平行,而当我们结束观看,回到本来的世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故事改变了,眼睛里满是离奇的锐角。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
说到离奇,就不能不说到凯茜·斯威尼(Cathy Sweeney),这个来自都柏林的作家把现代都市人的纠结、无聊、空虚 写得入木三分。我开始看斯威尼的作品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她的女儿,同样也是作家的露西·斯威尼·伯恩(Lucy Sweeney Byrne)一起做活动,主持人提到了伯恩妈妈的短篇小说集。
“我在书店看到那本书,”主持人说,“便拿起来翻了翻。第一句就把我震住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从前有一个女人,她太爱她丈夫的鸡鸡了,就开始把它装在午饭餐盒里带着去上班。(There once was woman who loved her husband’s cock so much that she began taking it to work in her lunchbox.)”
不用说,活动结束之后我即刻下单了斯威尼的书。
凯茜·斯威尼擅写超短故事。这个集子里的三个故事是我选出来的,拿去问她要不要取个名,她就说不如叫《三个爱情故事》(“Three Love Stories”)吧,我忍俊不禁。“爱情”这个词她点得实在是绝妙,充满了反讽。不用说,她的故事们是借“爱情”之名写生活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换言之,是“反爱情”。同样“反爱情” 并有一个绝妙标题的还有露西·考德威尔(Lucy Caldwell)的《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All the People Were Mean and Bad”):疲惫的母亲、总是缺席的丈夫、令人窒息的长途旅行、哭闹的女儿和怀着不明善意的陌生男人,第二人称的叙事,正像是孤索的女主角在喃喃自语——读这些故 事,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王小波式的问题:到底人生中的相遇是看似毫无意义,实则意味深长;还是表面上充满深意,本质却毫无意义?

电影《晒后假日》
妮科尔·弗拉特里(Nicole Flattery)的《欢迎光临》和温迪·厄斯金(Wendy Erskine)的《格洛丽亚和马克斯》(“Gloria and Max”)从不同的侧面来讨论这个存在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故事看似说的是个体人物的相遇,实际上又各自映着大时代的阴影:在弗拉特里的故事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都柏林;在厄斯金的故事里,是“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之后的贝尔法斯特。
***
贝尔法斯特,光是这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紧迫和张力。“有人说我们这些人只会写‘北爱尔兰问题’,但只要是一个北边的故事——不管故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哪儿可能和‘北爱尔兰问题’无关呢?”我的一个北爱尔兰的作家朋友有一次对我说。
“北爱尔兰问题”是爱尔兰岛上一个巨大的伤口,这伤口被切得太深,腐烂、疼痛得太久了,就算是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被打了麻醉剂、缝合了起来,才刚刚要开始愈合,又重新被脱欧的种种波澜撕扯开,汩汩流血。
路易斯·肯尼迪(Louise Kennedy)的《剪影》(“In Silhouette”)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鲜血的故事,一个家 庭的破灭,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失去兄长,寻找一份似是而非的爱情。第二人称、现在时,把过去和现在,伦敦和北爱尔兰织成了支离破碎又交错相连的一卷。
同样是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丹妮尔·麦克劳克林(Danielle McLaughlin)的《部分获救者名单》(“A Partial List of the Saved”)则像是一出轻喜剧,然而,当这轻喜剧发生在北爱尔兰,却有了更多的意味。故事里面没有人死去,但他们的旅途的背景中却满是亡灵:泰坦尼克号的遇难者;被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英国部队杀掉的爱尔兰 人,他们的铜像在乡道边立了将近一个世纪。
也是在贝尔法斯特,简·卡森(Jan Carson)的笔下栩栩如生的是这座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和底层人民,他们都在身体和精神的疾病里煎熬着。他们找到的救赎是一个从波兰移民来的姑娘,传说,跟在这外国姑娘的身后跳入泳池里,就会有奇迹发生。

电影《风吹麦浪》
在这辑的最后一个故事里,我们将回到都柏林,却发现梅拉图·乌切·奥科里(Melatu Uche Okorie)所写的都柏林和我们从凯茜·斯威尼那里所读到的那个城市大相径庭。一群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难民聚集在都柏林的临时安置所里,煎熬、焦虑,而又无比鲜活。奥科里这个“新爱尔兰人”作家在《小旅馆的这日子》(“This Hostel Life”)里一开头就干了件非常爱尔兰的事——拿自己人开涮:“你知道呐些个尼日利亚人的,他么时时刻刻都想干仗。”像所有其他卓越的爱尔兰作家一样,在奥科里的故事里,英文作为文学语言被拆开解构,又以有机的、地道的方式组合,再响起来,让我们听到众生的声音,各有特色、轻重、乡音,相互间顶嘴、骂架、揶揄,通篇喧杂却又声声入耳,句句都写在又痛又深的现实里。
***
2017 年的夏天,我推着刚刚满月的儿子到都柏林卡布拉(Cabra)的一间诊所,准备给他打预防针。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我的手机里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写邮件的人是露西·考德威尔,她说她从《爱尔兰时报》( The Irish Times )的文学编辑那里得到了我的邮箱,希望我不要介意她冒昧地来信,她说她正在着手编辑下一年的费伯爱尔兰新小说集( Being Various: New Irish Short Stories ),准备收入总共二十一位现在爱尔兰文学界的代表性作家,她又接下去说:“作为小说集的编辑,我想要重新思考‘爱尔兰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很想去拓宽这个概念,这概念应该包含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从别处来但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他们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给这小说集写一篇小说。”——当时,我一手抱着不断扭动的婴儿,另一只手握着隐隐发烫的移动电话,不确定自己是否 因为过度缺乏睡眠而产生了幻觉。

露西·考德威尔主编的爱尔兰新小说集封面
“‘爱尔兰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Irish writer?)好几年以后,编着这一期爱尔兰文学特辑,我的脑子里回响起来露西当时问的这个问题。我应该以什么准则、什么要求——如果我有这个资格的话——去选择收入这一辑的作家和小说呢?
在我看来,爱尔兰作家都和英文有着复杂的关系,从乔伊斯开始,他们就总要颠覆和解构这原本来自殖民者的语言,把它变得本土,古怪,自我,满是新意;爱尔兰作家们都是创造声音的高手,叙事声音也好,对话也好,句句都有棱有角,栩栩如生;爱尔兰的作家爱幽默和讽刺,不管故事的底色如何苦难压抑,他们永远都可以苦中作乐,让你大笑出声;爱尔兰作家也很会抒情,虽然他们一般不轻易这么干,但一旦抒起情来,一定是要“山无陵,天地合”的——多年了,每次想起《死者》的结尾,我都要流下泪来。
归根结底,爱尔兰的小说家和天下所有的小说家一样,其实是最我行我素的。当小说家进入他们的故事里,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切别的事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变得不重要也不存在了,唯一要紧的只是眼前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风景、世界不断扩大,充实着物品的细节、声音的余韵、植物的触感,将最终覆盖并取代小说家肉身所在 的、所谓真实的世界。
现在,是进入故事里的世界的时候了。
2022 年 8 月,英国诺里奇
▼
《单读 32·寻找救生艇:爱尔兰特辑》
现货发售中

▼
加入单读 2022 订阅计划
也可获得《单读 32》
▼
新的一年,继续同行
▼寻找救生艇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这里的人永远在苦难里爬行,吐出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
李峋第一次对朱韵说我爱你 想永远在嘈杂世界的角落……
许凯 这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s动吗,在横店的时候想逃离横店……
二舅们不该被困在苦难里
王开东:寻找自己的句子
弗里达·卡罗:用苦难浇灌的墨西哥玫瑰
让人大彻大悟的句子,句句激励人心!
封神里的他地位很高,但死后还被人烧了两次,真是悲催
幽梦影7个文采飞扬的句子,惊艳千百年,让人忍不住背下来
拿什么面对苦难?来自王小波、黑塞、薇依们的回答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66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6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27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27